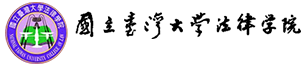law
2010年3月5日工商協進會工商講座演講紀要:環境永續與產業發展的雙贏策略
環境永續與產業發展的雙贏策略
演講人: 葉俊榮教授
整理者:莫冬立、郭思岑
然而,從臺灣的實踐看來,
事實上我們所處的環境是一個不完美的環境,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現實:不完美的社會與複雜的決策環境。
上述關於決策環境的討論與今日的主題中的「永續」
(一)環境影響評估
企業設廠的環境影響評估一直是企業與環保團體很重視的面
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環境影響評估?
以核准企業設廠或開發道路為例,
環境影響評估目前的運作即有上述事權分散的問題,
政府部門事權的不統一也引發並惡化環評其他的問題,
特別要進一步討論的是決策與環境因素考量的分離。
除了上述問題之外,
另一個例子是環境責任,最著名的案例是RCA事件。
RCA事件顯示的是環境污染的損害賠償責任人不清的問題
臺灣也有相當多環境責任所產生的損害或紛爭,
財務與風險分配是目前環境責任最重要的內涵,
以上以環境影響評估與環境責任在臺灣的實踐為例,
從許多研究來看,
企業善用環保標準獲致更大競爭力的例子最明顯的是Toy
臺灣是一個以外貿為主的經濟體,不能輕看國際標準,
面對越來越高且越來越普遍的環境保護規範,
以與我最切身的法律服務業而言,
企業遵行環保標準的成本是不同的,
採行總量管制,
*本文同步刊載於全球工商2010年4月號。
氣候變遷與經濟誘因: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簡介—兼及對經濟誘因管制的省思
全球環境政策與法律專題討論
SEMINAR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授課時間:星期一 第七、八(法1401)
氣候變遷與經濟誘因: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簡介—兼及對經濟誘因管制的省思
葉俊榮/張文貞 課堂演講
曾燕倫/呂尚雲 整理
2009.12.14
壹、對經濟誘因管制之省思:放諸四海或因地制宜?
美國自1960年代開始反省傳統的命令控制式(command and control)管制模式,並在各行政領域上大量採擇經濟誘因管制模式。目前此種以經濟誘因作為行政管制工具的理念,可以說在全球各國均已蔚為風潮。經濟誘因奠基於經濟學「人性自利」、「理性人」、「自由競爭」等基本假設,考量「成本」與「效益」,推崇「市場機制」,將理性及效率的理念奉為圭臬。在今天,無論是在學理上或政策實踐上,面臨千頭萬緒的管制議題,經濟誘因往往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政策工具,可以用來處理各種複雜而交錯的議題。然而,經濟誘因取向的政策工具,並非萬靈丹,也不是完全沒有因地制宜的考量。
首先,從管制目的達成與否的觀點來看,經濟誘因的管制模式以人性自利作為前提,認為經濟誘因可以驅使人們改變行為模式,進而達成管制目的。不過,人類的行為模式是否真的必然因為經濟誘因而改變,仍有討論餘地;而人之所以改變行為模式,可能因為各種其他的政治、社會或心理因素。例如,汙染情形之所以受到控制而減緩,可能是由於人的觀念改變,重新省視與大自然的關係;也很可能是因為科技日新月異,不斷有降低汙染的新發明或發現推陳出新,乃至於即使在不改變生產模式的狀況下,也能減少污染。即使經濟誘因取向的政策工具有其功能,也應該同時觀察並審視其所帶來一切有利或不利的效應。經濟誘因所衍生出的經濟利益本身是價值中立的,管制結果的好與壞,端視管制者對之如何加以運用。
其次,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經濟誘因之所以在美國或者其他國家成功作為一種政策工具,相當程度內也跟這些國家特定的歷史脈絡或發展背景有關;對於可能植基於不同歷史脈絡或發展背景的國家而言,在全盤採納經濟誘因此種政策工具之前,是否也應該對其政治經濟的發展脈絡作相當檢視,思索經濟誘因政策工具的採擇會帶來何種在地的變數與衝擊?以台灣為例,在民主化之前,台灣經歷長期黨國體制的統治,政治與經濟都緊緊的操控在統治者的手上,政權與金權合一。黨營或國營事業便是這種發展背景下的產物,即便在民主化的今日,這些由黨營或國營事業轉型的各項事業仍在台灣經濟體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關鍵勢力。在此種發展歷程與社經條件之下,在公共政策工具上不加思索地選擇經濟誘因作為管制手段,是否全然適當?是否符合歷史及補償性的正義?特別是在環境管制上,當牽涉到環境價值與各種利益錯綜複雜的糾葛時,經濟誘因式的政策工具是否可能過度偏惠市場及企業,而忽略無法以數值計算的歷史與環境的正義?如何充分考量獨特的發展歷程與社經條件,並搭配其他管制工具或作法,在台灣採納符合公平正義且具有效率的經濟誘因取向的政策工具,是未來的重要課題。
貳、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簡介及發展現況
氣候變遷的議題無疑是未來各國必須面對的重大議題。在國際規範上,由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發展出的規範架構,是目前全球因應氣候變遷議題的主要機制。我們有必要了解UNFCCC的規範機制,並掌握國際上因應氣候變遷議題的現況。目前正逢UNFCCC第15次締約國大會,同時也是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國大會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世界各國齊聚一堂商議因應氣候變遷之道,全球環境正處在關鍵的轉捩點,身為法律人的我們不能不予以關心及重視。
在哥本哈根會議舉行之前,美國聯邦環保署就已經在12月7日公布認定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六氟化硫等六種溫室氣體,為聯邦〈潔淨空氣法〉(Clean Air Act)中所應管制之「危害公眾健康與福祉」的汙染物質。原先聯邦政府希望透過〈潔淨能源與安全法〉的立法來管制溫室氣體,但立法過程並不順利。環保署現在透過此一公告,將可以開始對溫室氣體排放採取聯邦層級的管制措施,影響重大且深遠,某種程度也代表各國因應氣候變遷的措施已經到了迫在眉睫之際。美國聯邦政府此舉,也許是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也或許是歐巴馬總統所領導的新政府展現不同的視野角度與思維。總之,美國將溫室氣體納入與其他危害人體健康的空氣污染物質同樣層級的管制,且採行的不再是間接、勸誘式的管制,而是直接從汙染源來著手進行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管制,不僅將影響此次哥本哈根會議的諮商,也會對將來各國在溫室氣體管制上發生重大影響。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的關係,可以母與子的關係為譬喻,是很典型「公約及其議定書」 (convention-protocol)式的國際規範體制。作為公約主體,UNFCCC本身主要是提供一個世界各國參與並凝聚共識的場域,公約本身並沒有具體或強制的規範。UNFCCC的規範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確立「共同但差別的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意即在公平的基礎上,各締約國應依照其不同的能力,對保護氣候系統應負擔不同的責任;而已開發國家在因應氣候變遷及其不利影響上,應負擔主要的責任。至於其他因應氣候變遷更具體的規範內容,則由公約底下各個子規範形成並落實,京都議定書便是子規範的其中之一。今(2009)年12月7日到18日在丹麥哥本哈根所舉行的會議,便包含了兩個主要的子會議,一是公約第15次的締約國大會(the 15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15) ,目前公約締約國有192個國家;另一是京都議定書第5次成員國大會(the 5th Meeting of the Parties, COP/MOP 5)。估計約有來自各國政府、工商業團體、非政府組織等共15000人,由全球各地前來共襄盛舉 。由於台灣並非聯合國會員,因此只能由民間組織以非政府組織的身分與會。可喜的是,台灣也有獲選代表台灣出訪哥本哈根的學生「青年大使」。事實上,歷來的COP大會,台灣都有關注環境議題的人士主動參與,當中更不乏年輕的學生。此次哥本哈根會議的主要目標,就是要訂出「後京都議定書時代」的中程與長程減碳目標。
事實上,UNFCCC的發展歷程可以由幾個關鍵時點來觀察,分別是1990年、2008-2012年、2020年及2050年。根據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規定,各國必須以1990年作為基準年,2012年作為檢證年,在2008-2012間,各國必須達成議定書所設定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2012年後,將要有更進一步的減排目標,並以2120年作為中期目標,2050年作為長期目標,檢證因應氣候變遷的成果。值得我們密切注意的問題是,今年是2009年,離京都議定書設定的2012年目標還有三年,但各國卻已經討論起2012年之後的情勢。這其中多少蘊含有各國希望跳過2012年的檢證標準,而要早一步地全面洗牌再重來的姿態,這種態勢引起許多環保團體的憂心而群起抗議,但也讓很多目前看來已經達不到2012年目標的國家暗暗鬆了一口氣。
今年的第15次締約國大會(COP15)要討論的重要議題,包括今後中程與長程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以及新的檢驗基準年,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的減排義務差異的釐定,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的資金分配與技術開發與轉讓等。此外,新的減碳目標協議的形式為何?是否要在公約中加入條款?還是繼續採行議定書模式?新協議的執行機制為何?是否要有強制力?如何協助最貧困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否有必要擴張規範使其及於原先京都議定書排除在外的其它溫室氣體、或是京都議定書所未規範到的國際海運業與國際航空業?今後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京都議定書中專為開發中國家而設的彈性機制,是否應趨於嚴格以確保環境及生態的安全與完整,抑或應予放寬?此一機制中是否要納入未經證實的碳捕捉(Carbon Capture)或碳儲存(Carbon Storage)等相關科技,而允許既有的燃媒能源站繼續運作或增設?應否包含抑制伐林(尤其是針對開發中國家的熱帶雨林)等相關機制如「抑制伐林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計畫」(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REDD)?凡此問題,均為這次締約國大會所涉的重要議題。
不過,此次會議所面臨的最大難題,還是在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對於「後京都議定書時代」的協議並沒有共識。已開發國家認為,開發中國家排放量大,應共同承擔減量工作。開發中國家則認為如今氣候之所以暖化,是已開發國家過去所造成的禍害,基於公平正義,已開發國家理應負起較大減量責任。因此哥本哈根會議是否能順利完成「後京都議定書時代」的新協議,中國、美國的態度是關鍵。甚至,從全球各國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排名來看,可以認為溫室氣體減排議題幾乎能被簡化為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談判戲碼」(bargaining game),談判結果與效果都取決於中美兩國的態度。
參、台灣在全球氣候變遷時代下的定位及角色
台灣過去一直被拒斥於國際社會之外,面對全球氣候變遷此一重大議題,要如何積極參與於國際社會的相關規範機制呢?事實上,觀察國際社會因應氣候變遷議題的模式及趨勢,可以發現台灣無須悲觀。在國際社會的各場域,台灣往往受限於國家定位的問題,不得其門而入。但我們觀察目前國際發展的趨勢,可以發現有兩種超脫以「國家」為單位的新模式。在氣候變遷議題上,過去都是以個別國家為中心的思考,但這種思考模式最近已發生變化,使得國家利益本位在環境議題中不再是唯一的談判籌碼。
第一種是「向上沖」的模式,如歐盟的例子。歐洲以超越國家的角度,形成區域性的組織,這種模式將國家拉到區域性聯盟的角度,使個別國家必須跟隨所屬區域聯盟的標準,而得以整合各方資源。從歐盟今天成功的發展經驗來看,這種模式可能逐漸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第二種是「往下洗」的模式,尤其表現在聯邦國家中。以美國為例,各州政府與聯邦對於環境政策可能採取不一致的立場,各州得以從其觀點及利益發展對其最適合的環境政策與法律,甚至直接並主動地參與國際合作,美國加州、德州、麻州等州政府都有積極參與全球因應氣候變遷等國際合作的例子,不見得需要依賴聯邦政府。這種以國家內的各單元進行合縱連橫的發展方向,也有別於過去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環境法發展,值得我們密切注意及觀察。不管是「向上沖」或「往下洗」的新發展模式,都對台灣在全球氣候變遷的相關議題上,提供了更多的新思維及新可能。
氣候變遷與公民社會的角色:氣候變遷下公民社會之理論與實踐
環境責任制度之過去與未來—以訴訟作為環境問題的解決途徑
一位環境法律師的實踐:松菸環評公民訴訟實例分享
2009年12月29日環境法課程專題演講摘要
<一位環境法律師的實踐:松菸環評公民訴訟實例分享>
演講者:林三加(法律扶助基金會專職律師)
整理者:曾燕倫
中心主任葉俊榮教授開設之環境法課程,於12/29日上課時邀請法律扶助基金會林三加律師,進行課程專題演講。林律師分享個人學思歷程,也分享今年2月親身參與松山菸廠保護老樹事件的經驗,並針對法院實務運作、行政機關執法、社區民眾參與、比較外國範例等議題,加以評論、提出倡議。演講完畢後的Q&A時間,同學提出個人生涯規劃、國內制度改革等相關問題,林律師一一回應說明。以下為林律師演講之重點摘要:
1.個人學思歷程
林三加律師現職法律扶助基金會專職律師。民國76年進入台大復健系,77插班台大法律系,當時導師為葉俊榮教授,與葉老師學習,受益良多。80年自台大畢業之後,自83年開始擔任執業律師迄今。大學時期,林律師於醫學院就廣泛參與環境相關之課外活動,例如協助台灣環保聯盟的反核禁食活動,於反核劇場擔綱演出等。律師執業時期,一開始係進入事務所工作,接辦一般民、刑、商務案件之餘,也有多次承辦環境訴訟的經驗,與環境團體接觸頻繁。後漸對事務所工作感到倦怠,放長假思考生涯規劃後,決心投入個人有興趣的環境公益訴訟。於是離開事務所並自己開業,也進入法律扶助基金會成為專職律師。
2.松山菸場保護老樹事件
2.1事件始末
97年10月,林律師接獲市民請求,希望能協助保全將被開發興建大巨蛋的松山菸廠中的老樹群。林律師於是向法院申請假處分,請求不得在環評審查通過前,移植松菸內之受保護樹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98年2月9日發出假處分開庭通知,開庭時間為98年2月27日上午10時30分。然而老樹群卻在開庭前的期間陸續遭到移除,印度橡膠樹、大葉山欖、楓香樹、錫蘭橄欖、榕樹等,皆於2月24日遭施工單位移除。以致2月27日假處分開庭當天,請求保全之標的將只剩一棵大樟樹。開庭當天清晨,台北市政府急著移除最後一棵大樟樹。當地民眾發動抗爭,林律師也到場關切,經協調後,同意下午1:00前不移樹。不料假處分聲請案開庭完畢後,法院竟沒有做出任何裁定。下午1:00過後,施工單位即要動工遷樹,當地民眾進行抗爭,以爬上樹木、環抱樹根、人身阻擋之方式阻止移除樹木,台北市警察局以違反集會遊行法逮捕護樹市民4人,護樹市民被控涉嫌妨害公務罪,遭警方留置長達近10小時才做筆錄,移送至地檢署,經檢察官偵訊後,於深夜11時許飭回,整個過程中林律師全程陪伴。次日各大報皆報導了此則重大消息。
2.2重要議題
由松山菸場保護老樹事件中,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1)環評制度中民眾參與的問題。民眾參與是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相當重要的因素,但是目前制度設計上是否有缺失,使得民眾不能實質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此外,環評法所建構之公民訴訟制度是參與式民主的落實,但是實務運作是否完善?
(2)制度條件的問題。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意義為何?應該具備什麼功能?是否能夠落實?本案例中,雖然已向法院申請假處分,請求不得在環評審查通過前,移除松菸內之受保護樹木,但實際上仍無法阻止樹木被移除。假處分制度似已淪於形式。此外,警方將受逮捕人長期留至於警局內而遲遲不為筆錄制作與移送,恐不利人權保障。這些問題,涉及的是保障民眾參與的制度條件。
(3)官方心態的問題。本案中,行政機關趁著法院開庭之前,趕緊將老樹移除,可見藐視司法與鑽法律漏洞的心態;法院開完假處分庭後,竟然沒有為裁定,可見無法體會環境議題的重要性,也不了解本案情況的急迫性。行政機關與法院的觀念與態度,相當不利於環境價值的落實。
(4)法院角色的問題。本案中,檢察官最後對於護樹市民予以不起訴處分。然而,該不起訴處分書中的論理似乎流於形式,並沒有認真析論本案的關鍵爭議,沒有針對問題的核心提出見解與主張,平白錯失發揮司法功能的良機。
3.國外的公民參與實踐情況
從國外民眾參與的事例,可以思考台灣目前的情況:
3.1 Julia Butterfly Hill的故事
在美國,Julia Butterfly Hill (1974~)的事蹟相當著名。她23歲那年(1997年),為了阻止開發,爬上一棵高55公尺、600歲的紅木樹,長達2年之久,後來終於「下樹」,下樹後還一度被愛樹人士批評其背叛老樹。與台灣的案例相比,值得省思的是,美國關心環境的人士為了阻止開發,能夠爬上樹長達2年,而後自己下樹,但是台灣的佔樹抗議卻只能有2天 (2009.2.27~3.1),還遭到警察逮捕。公民參與的社會,市民關心環境的訴求,如何在體制內運作?此外,美國社會普遍都有關心環境的熱情,2年後下樹都還會被斥為背叛,反觀台灣,社會上一般看待護樹市民的心態,又是如何?
3.2美國紐約中央公園的誕生
美國紐約中央公園廣達843acres /3.41平方公里,是今日都會區裡難得一見的大綠地。中央公園的誕生,必須歸功於Andrew Jackson Downing (1816-1852)這位有遠見的人士的奔走。紐約市於1851年立法徵收土地,創設了中央公園。市長Kingsland於1851年4月5日向市議會報告時說:「徵收土地來建設中央公園是必要的,公園提供健康、快樂、舒適,特別是為了窮苦的老百姓之利益。這個公園會證明創設者的智慧,因它將確保未來後代擁有乾淨的空氣、純真健康的快樂。」紐約中央公園的源起,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保障民眾最低限度的環境品質,使得環境不致成為奢侈品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對於社會底層的人士而言,而這需要民眾參與促成。
4如何成為一個好的環境律師
一個好的環境律師,必須具備三項條件:知識、專業、熱情。因為環境議題橫跨各領域,所以必須具備充足且無侷限的知識程度;因為法律人必須以所學來引領環境議題制度面的發展,所以必須具備法學專業素養;因為環境議題需要長時間投入關心,所以必須對環境充滿熱情。
未來大家可以幫忙的地方,包括法律扶助基金會(成立環境法律中心)、原住民法律中心、勞工法律中心、婦女及性別平等中心(目前皆尚在建構中)、環境法律人協會(籌設中),以及其他NGO。期盼有更多人投入環境律師的行列。
Q&A
- 環境議題既然牽涉到各種專業背景,法律人應如何確保在環境法議題的主導性與獨立性,而不被其他領域的專家牽著走?
答:在環境法的議題上,法律人應扮演的是「提綱挈領」的角色。面臨問題時,必須能夠把問題「綱要」先抓出來,能夠將相關爭議條理化,掌握到具體的問題點之後,再由其它領域的專業來個別解決。
- 目前在台灣從事公益訴訟的律師在生活上是否比較難以為繼?
答:其實從事公益律師有多種方式,比方說可以加入NGO組織,接受薪水專職從事公益訴訟,也可以同時承接一般業務兼作公益訴訟。公益律師生活也許沒有其它律師富裕,但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端視個人對於物質生活的要求程度以及興趣之所在。
Citizen Suits for Better Environment: A General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in Taiwan
Citizen Suits for Better Environment: A General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in Taiwan
For
The 9th Asia-Pacific NGO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 (APNEC9),
November 20-21, Kyoto
Jiunn-rong Yeh,
Professor of Law, College of Law, NationalTaiwanUniversity, Email住址會使用灌水程式保護機制。你需要啟動Javascript才能觀看它
INTRODUCTION
The burgeoning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over last 2 decades has robust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major area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Among which,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one that attracts most public involvements in divergent forms, including representation in decision-making bodie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hearings, demonstration, sit-ins, and litigations. In recent years, concerned citizens or environmental groups have, more frequent than ever before, taken the form of litigation to address their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his was made possible, among others, by legislative efforts that make possible for citizen to sue in the courts for th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eeks to sketch the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 suits (公民訴訟)in Taiwan and analyze its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backdrops. Though most cases will be reviewed, the Taidong Beautiful Bay (台東美麗灣) litigation, a 2008 landmark case in which the plaintiff environmental group won for the first time, will be the highlight. This analysis is followed by a general review on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current practic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democratization has been the driving forces for current burgeoning environmental citizen suits. Citizen participation via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will not only safeguard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empower civil society in caring “our common environment”
THE BEAUTIFUL BAY AND CITIZENS’ FIRST TRIUMPH IN THE COURT
In Taiwan, it was not until 1999 that the first citizen suit clause be written into law and not until 2008 that an environmental group plaintiff won in a citizen suit case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landmark case is known for Taidong Beautiful Bay litigation.
In December 1994, the Taidong County Government, in hop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its local tourism, signed with the Beautiful Bay Resort Co. a BOT contract, according to which the Beautiful Bay Resort Co. would build a resort hotel on the Sanyuan beach, situated on the eastern coast of Taidong County, and pay the Taidong County Government 5 million NT dollars plus 2% of annual revenue.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this project would take up 59,956 square meters, far over 1 hectare, a threshold set by the regulations authorized by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aw (EIAL), and therefore must go through the procedur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The Beautiful Bay Village Co., however, in February 2005, applied for merge-and-re-segmentation of the land, to which Taidong County Government permitted, thus separating from the whole bulk of land a piece of 9,997m² ( 3m² short of the set threshold), which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hotel building needed , so as to shied itself from the legal requirement of the EIA procedure. The plot was later disclosed by some legislators and environmental groups, and, in May 2007,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23 of EIAL, the Taiw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ion (TEPU) filed a citizen suit at Kaosiung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against Taidong County Government, demanding a order from the Court requiring Taidong County Government impose fine on the Beautiful Bay Resort Co. and suspend its construction right away.
The court first confirmed that the TEPU qualified as a public interest group to file a citizen suit, and then moved on to further reasoning on substantive matters. The very purpose of the EIAL, the court pointed out, is to lessen and prevent possible 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s by major constructions. Given the fact that this BOT project is to take up 59,956 square meters, not just the mere 9,997 square meters for the hotel building construction, to merge-and-re-segment the land in order to avoid the EIA process has violated the legal requirement of EIA. Failing to enforce the nondiscretionary EIA requirements, so ordered the Court, Taidong County Government should suspe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ject. Note, further, the Court also awarded NT$ 60,000 as attorney fees to the plaintiff, the first of this kind in history.
CITIZEN SUITS IN TAIWAN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Most of the earlier citizen suits in Taiwan involved a variety of issues such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dumping, reservoir-building, and so on, while cases in recent years were mostly EIA cases and the number is on the increase. Up to now, the courts have ruled 9 citizen suits brought by concerned citizens or environmental groups against relevant authorities, among which 6 were EIA cases. In these EIA cases, 4 of them are filed by environmental groups and 2 are filed by concerned citizens, signaling that environmental groups have taken the role as pioneers in environmental litigations.
Notably, what those cases have in common is that there were lawyers arguing in the litigation, the ratio far higher than in normal cases. Besides, taking a look at all the members in these cases, it appears that some cases share the same lawyers. It is noteworthy because there was rare distinct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lawyers in these matters. Some sort of social nexus thus must have played a role in it. Besides, EIA cases, compared to other cases, are significant in that they are more complex because their main issues on trial usually contain high-tension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e trend of environmental citizen suits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refore, implies that Taiwan’s social mechanisms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working and that they are gaining momentum.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In light of Taiwan’s experience, we see strong connection among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backdrops. These experienced could be analyzed in three perspectives.
First, social capacity-building plays a role. The very idea of a citizen suit, citizens filing a lawsuit for public interest, signifies the breakthrough from the traditional “right-based” thinking. Certain institutional factors such as citizens, inform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urts, are required to back it up. Right in the moment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case of Taiwan draws a clear distinction. In Taiwan, back in the time before going through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with freedom of association oppressed, information unable to be fully disclosed,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discouraged, and courts suppressed of its function, citizen suits were all but possible. Nowadays a vibrant civil society has become the hardcore capacity-building fo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for better environment.
Second, legislative strategy is also important. Due to the complicated legislative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al statutes, to have a citizen clause written into law is one thing, in what form to have it written is the other. And the latter undoubtedly weighs much in practice.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laws more often than not include citizen suit clauses, while most of them are one way or the other, confined in the scope of their application. Also, the existing dual judicial system in Taiwan, normal courts and administrative courts, has complicated the creation of the system righ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ird, the attitude of the courts is by all means a determinant factor. In fact, before the Taidong Beautiful Bay case, quite a few citizen suits had been filed, while those cases were finally either dismissed before reaching a substantial reasoning or ended up without one. Due to the constrained legislative structure, or to its past consistent conservative attitude, the courts stuck to the traditional way of “right-based” thinking, holding that one can resort to the court for remedy only when his/her/its right has been infringed upon(the so-called “subjective litigation”), and thus contradicted with the spirit of citizen suits.
In1998, the Justic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of Taiwan affirm in Interpretation No.469 the “right-base” argument, but on its ground loosened the requirement of it. The interpretation ruled that,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infringed right exists as the plaintiff states, the court must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law, the objects to which the law applies, the purpose of the law,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actors to fathom whether the law intends to protect the said right. Then in 1999, the first citizen suit clause was written into the revised Clean Air Act, and in 2002 the EIAL included the citizen suit clause, hence both the “subjective litigation” and the “objective litigation” are accommodated in Taiwan’s legal system ever since.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words used in these clauses such as “concerned citizens and public interest group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ubjective litigation and the objective litigation can not be easily drawn and may even be confused. At times it still depends on the courts to decide practically in every case whether it is to take a friendly check upon the issue of standing, or otherwise.
CONCLUS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re in essence issue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burgeoning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provides for soil needed for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for better environment. The Taidong Beautiful Bay Case is the best narrator of the story. Furthermore, the growing of the citizen suits in EIA area reaffirms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citizen suits in its assurance of procedural rationality in decision-making. By filing a suit for public interest, citizens give the court a chance to review the legality and rationality of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Taiwan’s experiences shows that, in practice, citizen suits, with the momentum of democratization, safeguard the environ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empower civil society in caring “our common environment.”
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舊公約與新挑戰--氣候變遷下國際生態保育公約的調整與回應
2009年10月8日歐盟氣候變遷論壇之講演紀要
演講者:葉俊榮
葉俊榮教授受邀於2009年10月8日歐盟氣候變遷論壇擔任引言,該次論壇主題為「後京都氣候談判:歐盟的經驗與台灣的挑戰」,論壇舉行的地點則為臺灣大學第一學生活動中心202展示室。以下為葉教授當日的演講紀要:
1. 公約與議定書搭配模式的成形
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FCCC)開放簽署至今,氣候變遷的問題逐漸規範化,有全球性的綱要公約,接下來還有議定書等的簽訂,這些規範不斷強化、具體化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京都議定書是一個中點,接下來是否有其他後續的議定書,值得觀察,但未來的議定書都必須在FCCC的架構下發展。FCCC以共同但差異的責任為基調,是一個結構紮實的公約,在今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之前,我們可以觀察到公約搭配議定書的模式似乎已經成形,甚至可能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FCCC的實踐經驗是,先簽署FCCC,數年後再根據公約簽署議定書執行公約內容。國際社群在過去曾考慮在公約中直接納入強制各締約國履行的條款,但這種綱要公約/議定書模式,改變了這種想法,未來公約的執行非常可能延續採用這種先簽署綱要公約後再以議定書規定具體履行義務的模式。
2. 檢證年與基準年對比模式的採用
京都議定書採採取檢證年與基準年的對比機制,應該也是未來發展的模式。過去對於達成溫室氣體的減量目標,雖有各種如個別減量等不同模式,但京都議定書採行的方式為設定1990年為基準年,以2008到2010年為達成年,並將締約國區分為附件一及非附件一國家,再對附件一國家分別設定不同的減量百分比。議定書甚至可以配合不同國家的發展狀況,調整減量的百分比。京都議定書設定的基準年為1990年,該年正好是OECD國家在GDP與溫室氣體排放量出現分離的一年。歐盟在最近再以2020年為基準,要求未來排放量降到20%到25%。這種採取檢證年與基準年的對比機制,應該也是未來發展的模式。
3. 直接管制模式與彈性機制之兼容並蓄
就管制工具而言,過去採直接減量管制模式,但FCCC後已逐漸建立彈性機制,例如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共同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ing)等,原來環境法的直接管制模式,已經與彈性機制發生兼容並蓄的現象,並交叉運用。歐盟過去雖反對美國主張的市場交易機制,但近來反而相當重視彈性機制,甚至是最強而有力採行市場交易模式的地方,例如歐盟建立了碳排放市場,並提供經濟誘因,利用多元的管制工具達成整體減量目標。然而採取這種彈性機制,將對發展中國家產生很多機會與挑戰。對台灣及其他快速發展國家,究竟要採用直接減量管制模式或還是進一步善用彈性機制,考驗著主政者的施政能力。
4. 附件一國家及附件二國家區別模式面臨重新洗牌
FCCC採取附件一國家及附件二國家的區別模式。原先是以OECD國家加上中東歐轉型國家為附件一國家,但這樣的區別長期遭受美國攻擊,質疑中國未能納入管制。的確,在後京都時代,這種附件一與附件二國家群的區別面臨重新洗牌。台灣在溫室氣體的減量上,究竟處於何種管制定位?縱使我們目前有政治外交上的困難,但在管制定位重新洗牌之際,又將再次彰顯此等問題。
5. 區域聯盟形式的發展
最後一點是我最近在研究的課題,我們發覺過去氣候變遷都是以個別國家為中心的思考,這種思考模式最近已發生變化。過去氣候變遷的參與模式,大都為利益模式所主導,但此一利益是以個別國家的利益為本位。然而以個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的國際談判,在現今的環境中則面臨困難。目前有兩種趨勢,第一種是超越國家角度,形成區域性聯盟、組織,這種模式逐漸成為未來發展趨勢,例如歐盟。這種趨勢沖淡以個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思考,將國家拉到區域性聯盟的角度,使個別國家必須跟隨所屬區域聯盟的標準,這種現象在歐盟特別明顯,我稱之為「往上沖」的趨勢。另外還有所謂「往下洗」的趨勢,有其表現在聯邦國家,例如美國。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的表現相當保守,但觀察美國情形時,不可忽略美國其實是有許多州所組成的聯邦制國家,各州也有其憲法所賦予的權限,美國各州與聯邦政府間的關係跟歐洲各國與歐盟間的關係很類似。以加州為例,加州的人口或排放效應,可能抵得上很多歐洲國家,加州在氣候變遷一事上的立法與執法決心,也與歐洲各國不相上下,但加州在溫室氣體減量的努力,卻被放在「美國」這個國家架構下評估。類如加州這種次於國家的發展方向,也是以國家為中心的另類發展方向。以上兩種變化,對台灣都有相當的啟示。
我希望藉由關心氣候變遷議題在歐盟的發展,思考台灣未來的對策。以上對於歐盟的現況的瞭解不僅是從科學角度,也包含政策與法律方面,這些部分國內很少經營,所以很希望能跟各位探討這些課題。我們的政府在做政治決策時,也不應忽略這些很重要的議題,或許對台灣真正具有影響力的,是這些政策、法律層面的決定,而不是科學層面的發現。以上幾點與各位分享,希望能對各位有些啟發。
在演講後的討論時間,葉教授又針對參與者的提問,分享了以下看法:
1. 貿易政策的環評必要性ECFA這種自由貿易的協定有無環境影響評估的必要?
過去的貿易政策往往未就環境影響層面進行考量,但這確實需要作政策環評,而且是翔實具體的評估。目前對於ECFA對環境會有如何的影響,無法立即有明確答案,但我很贊同要就這樣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
2. 各國自行訂定溫室氣體減量法各有其不同背景與考量
訂定溫室氣體減量法的國家,最早僅有日本跟瑞士。瑞士因為是中立國,不希望捲入國際集團的紛爭,所以透過內國立法,維持自主性。日本訂立溫室氣體因應法則是考量教育,尤其強化中央與地方以及政府與國民的共同責任。台灣作溫室氣體減量立法背後的理論依據,乃是基於實際上無法參與國際,國會也沒有機會進行公約的「批准」,而採取與瑞士類似的作法,透過國會的立法來彰顯國民意志,跳過公約的簽署與批准,實質上作自主的連結國際規範。
氣候變遷與環境影響評估: 跨境環評議題的新視野
氣候變遷、能源管制與能源安全:台灣觀點與國際視野
葉俊榮/張文貞 課堂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