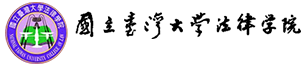law
2011秋-環境法課程簡介
本課程名稱雖為「環境法」,但內容並不以法律為限,而涵蓋環境問題的成因、因應制度及執行成效的評估與檢討,強調法律制度與環境問題的關連與運作。課程內容結合生態、經濟、政策、科技等面向,做政策與法律的分析與探討,並以臺灣實際面臨的環境制度問題作為具體討論對象。本課程分為六大部分,共有21個單元,分別為:發展脈絡與研究方法(單元1至單元3)、制度結構(單元4至單元7)、制度單元(單元8至單元13)、管制領域(單元14至單元17)、國際環境議題(單元18至單元19),以及永續發展與環境法的挑戰(單元20至單元21)。
2010秋-環境法課程簡介
本課程目標在於讓同學瞭解環境問題背後的制度面因素及其如何影響環境的現況。課程名稱雖為「環境法」,但內容並不以法律為限,而涵蓋環境問題的成因、因應制度及執行成效的評估與檢討,強調法律制度與環境問題的整體界面。本課程分為六大部分,分別為:發展脈絡與研究方法、制度結構、制度單元、管制領域、國際環境議題,以及永續發展與環境法的挑戰,每一個部分又再區分成數個單元。課程內容結合生態、經濟、政策、科技等面向,作政策與法律的分析與探討,並以台灣實際面臨的環境制度問題作為課程的具體討論對象。
98年度第1學期環境法課程介紹
葉俊榮教授每年均於大學部開設環境法課程,目標在於讓同學瞭解環境問題背後的制度面因素及其如何影響環境上的現況。課程名稱雖為「環境法」,但內容並不以法律為限,而涵蓋環境問題的成因、因應制度及執行成效的評估與檢討,強調法律制度與環境問題的整體界面,結合生態、經濟、政策、科技等面向,作政策與法律的分析與探討,並以台灣實際面臨的環境制度問題作為課程的具體內容,討論的議題包括:環境權的論爭、環境立法與環境管制結構、環境管制與民眾參與、公害糾紛形成與處理、污染防制費的徵收與經濟誘因、環境影響評估、環境責任法、環保的行政訴訟、環境協商、環境行政程序、國際環保議題、國際環保公約、永續發展理念的形成與發展等。
◎指定教材
A. 葉俊榮,環境政策與法律,臺大法學叢書(六三),2001年新刷(編號為A1至A10)。
B. 葉俊榮,環境理性與制度抉擇,臺大法學叢書(一一○),1997年 (編號為B1至B10)。
C. 葉俊榮,環境行政的正當法律程序,臺大法學叢書(七六),2001年新刷(依章節順序編為C1至C6)。
D. 葉俊榮,全球環境議題:臺灣觀點,巨流出版社,1999年(編號為D1至D10)。
100年度第1學期課程介紹
◎課程概述
人為因素所導致的氣候變遷,造成了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的劇烈衝擊,漸漸在科學證據的有力佐證之下,成為無法否認的事實。自1980年代開始,氣候變遷議題即躍上國際舞台,成為國際社會關切的重要環境議題之一。晚近以來,氣候變遷對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影響,已經到了無法忽視的程度。如何減緩及調適氣候變遷的效應,遂成為國際社會今後必須共同努力的目標。氣候變遷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議題。氣候變遷具有「大尺度」的時空特殊性。時間上,氣候變遷的特色是延續性與累積性;空間上,氣候變遷是跨國界的議題。此外,氣候變遷更是個跨科界而無所不包的議題,科際整合的色彩相當濃厚。這些特性都是因應氣候變遷所不能忽略的關鍵,也正是這些特質使得氣候變遷成為全新的特殊議題,而傳統的法律與政策的框架,顯然不足以應付這項挑戰。如何建構一套適切的氣候變遷法學,是本課程著眼的核心問題。
本課程由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關鍵議題(targeted issues) 、制度規範(norms)等四個面向為主軸切入,思考氣候變遷法學的建構。首先思考權力角力的國際舞台上,氣候變遷議題的發展脈絡以及所面臨的問題;其次探討氣候變遷相關的重要政策工具,包含經濟誘因工具、環境影響評估、環境責任法制等,分析其利弊得失;接著關切幾個與氣候變遷休戚與共的重要議題,包含能源、貿易、人權與正義、自然災害與調適等等;最後進入制度與規範面,從立法政策與司法部門,以及法律原則與國際法,分別探討傳統法律架構面臨何等衝擊,以及應該如何作調整。
學生短評精選- 萬庭威
*本文為回應12/21葉俊榮教授<氣候變遷與經濟誘因>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揚棄法教條學、擁抱法律經濟分析:方法論上的進步?
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存在衝突?
眾所周知,大陸法系最大的特色在於由羅馬法所派生,並以一部成文法典作為法律的本體。台灣在繼受法律的過程中,主要係受德國法之影響,而德國現代哲學發展之高潮在於自康德之先驗理性論以至於黑格爾的辯證理性論(即一般所稱之德國觀念論),雖說無法斷定哲學思潮對於法學之影響程度,但如此的發展與預設法典中存在先驗價值的觀點非常對味。是故,若法典有其內在的先驗價值,法律人的工作便是開展、發現法律,而不能去創造法律,這即是概念法學之所以形成的基本條件之一。德國後世雖有自由法學派強調法官的自由判斷,但並未形成法學界主流,反而或多或少與法律社會學界更為密切;而概念法學之後的利益法學以及當今位處主流學說的價值法學,更主張將法律的價值置於當事人利益衝突下,法官適用法律應考慮的是如何運用法律將當事人之利益衝突做調和,使個案中的目的性要求衝破法律規則。就此法律思想而言,亦指出法官作為裁判者是如何在當事人利益衝突之間做抉擇,成文法典的角色的只是一個工具箱。這個工具箱雖無法將所有可用的工具都收納進來,但仍可永遠預留一些空位(一般條款),在困難的案件中尋求新的工具以納入法律工具箱。
相較而言,英美法的無法典特性就不會有上述的問題:法官身為法律創造者,在個案中所為之判決並非發現法律,而是更積極地參與當事人間利益衝突的解決。相對的,判決先例原則就有點類似於成文法典的作用,藉由過往經驗與智慧的累積奠定法律基本原則;而一旦法律原則在個案中的實施將造成荒謬的結果,則可用衡平法原則加以補救之,故衡平法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法典中的一般條款。
綜上所述,普通法與大陸法雖然對法律原則的產生想像不同:一則基於無預設的經驗主義立場,另一則偏向先驗理性的肯定;但對於法律人作為決策者,不能無視現實世界的價值衝突這一點立場上並無二致。因此,在台灣的時空背景上若出現死守法教條學的法匠,問題似乎不真的出在學說或是法系不同的問題,而更應該是:在法律繼受的過程中缺乏了什麼要素使得盲從成為一個可行、甚至是大家所偏好的選項,而非仔細開展法律教育與思考的理論面?這個問題似乎不是單純用法律體系上的不同就可以解釋,而更需要其他的方法來考察。
京都議定書裡的經濟誘因到底有沒有用?
在哥本哈根會議以失敗收場,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全球暖化管制新體系看來遙遙無期時,對經濟誘因作為京都議定書主要管制工具進行反省在時機上似乎再恰當不過。京都議定書允許三種彈性機制供各國使用:joint implementation、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以及emission trading,前兩種機制可以產生額外的碳排放權,而多餘的碳排放權則可在emission trading market中自由交易,供有需求者購買。
關於joint implementation以及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所產生的碳排放權於京都議定書中雖要求必須是額外於原狀況的減量,但要如何計算一個JI計畫或是CDM計畫產生的碳權真的是額外,則有許多爭議。除了計算方式本身在科學上已莫衷一是之外,在牽涉開發中國家的CDM機制裡,實踐上還曾有已開發國家到開發中國家進CDM獲得碳權的方式居然是砍掉原有雨林,再重新種樹以便「植樹」這一項名義獲得碳排放權。若缺乏良好的科學計量方法,又沒有強而有力的執行、監督機制,縱令JI及CDM原意是用經濟誘因的方式達到減量的目標,仍然會因為這兩個因素而使得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關於emission trading,在京都議定書中所採的模式屬於baseline and credit交易,而非其他區域性的emission trading market多以cap and trade方式進行。Baseline and credit交易的缺點主要係來自上一段所提及的兩個原因,而無法確保交易的碳權是不是真的已經實質減少排放;而cap and trade理論上雖然只要cap設定好,並嚴格執行之就可以達到減量目的,但在現行的cap and trade機制中,初始的排放量大多用grandfather clause無償給予,而這具有相當大的道德風險:過往污染越是嚴重的公司,在碳交易市場中反而是銀彈最足的,而且這些銀彈還不用花一毛錢就可以取得。此外,在現行區域碳交易機制中的基礎條約裡多具有連結條款,允許其他非同一區域所產生的碳權進入區域碳交易市場,而可能使cap往上漂移,而最終根本沒減量多少。
經濟誘因作為管制手段並非不可行,但在有能源稅、碳稅等等直接處罰排放者、獎勵清潔者的手段可用時,我實在看不出來這些得來極為容易的碳排放權及其交易對於實質減量有什麼幫助,尤其是cap根本漂浮不定、又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情況下,買空賣空的情形只會更加嚴重。
法律經濟分析與經濟誘因:經濟學帝國主義?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界裡似乎以其科學性自豪,不外乎是因為大量的模型建構以及數學的運用。但這樣的自豪轉譯到真實社會中往往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預測失敗。我個人認為問題是出在於數字跟個人、集體行動是兩種不同的範疇,無法相互化約。在數字的隔閡之下,研究者對於真實社會的理解彷彿隔有一層膜,藉由選擇性排除不在模型之外或難以量化卻很重要的變因,我們就看到很多失靈的管制措施在經濟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一點用也沒有,像是京都議定書的彈性機制就是一例。
同理,面對法律研究本身,為什麼經濟分析在方法論上是一種好的工具?難道是因為它運用的數學令人目眩神迷?還是它將各種法律原則化約為理性選擇以為解釋,滿足一套打天下的科學一統論夢想?在批評法教條學的不切實際時,我個人認為解決方式不是急著找另一套唯一方法去打掉它,而應該對法律的本質更加開放地看待,並暫且認為法律是一個獨立的存在,無須急著用理性選擇去化約法律原則。
法律經濟分析確實提供了不同於傳統法學的觀點,並在效率作為一種價值的情形下別具意義。但理性選擇論到底能不能化約其他法律原則,我個人持高度懷疑的立場。同時,經濟學也不是完全數學化的一門學科,然而一般提到法律經濟分析卻不會想到歷史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與方法,這種忽略是有意還是無意,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學生短評精選-洪國華
法律經濟分析目前被認為是不同於傳統之法學方法,有別於採取歷史論、立法論、解釋論的方式,而希望使得在法律適用的判斷上,其結果實質上對於社會有更大的利益,或是使得法律系統的運作可以減少所需的社會成本。法律經濟分析對於傳統法學方法的質疑也正在於是否僅為追求法律解釋邏輯一致性,如在是否違反立法者的本意、擴張解釋或是類推適用等在此多作爭執,而忽略法律適用應考量社會而非社會要按照法律邏輯無矛盾的運轉。
學生短評精選-林季陽
學生短評精選-李新恩
學生短評精選-李崇菱
Recognising the future threats to their survival, Chinese leaders in 2006 embarked and endorsed a new commitment to new energy technology, and boosted funding for research and set targets for installing wind, solar panels, hydroelectric dams, and other renewable sources of energy.[4]In 2008, China became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in the world, and renewable energy alone attracted USD 15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So long as China can ensure a continued growth rate of fifteen percent per annum would ensure that renewable technologies would be equal footing with oil, gas, and coal in the next two decades[5]. China’s President Hu Jintao, declared to the world in October this year China must “seize pre-emptive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energy revolution.” The rate and scale of China’s ambition is astonishing. David Sandalow, the United State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an interview for New Yorker article, remarked on China’s effects in renewable energy is “extraordinary”,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American, is clear: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makes investments, we are not competitive in the clean-tech sector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Whe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eenhouse gases emitter, energy policies have gone differently.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nounced in April of 1977 when America went into the hunt for new energy sources, as result of the second Arab oil embargo, as 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 Public investment in energy research was nearly quadrupled in fund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fortably lead in clean technology by the mid-nineteen-eighties, where more than fifty per cent of the world’s solar cells and ninety per cent of the wind power were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 Regan administration came into power, the deregulation and acting on a pledge to abolish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investment in energy research also were reduced, which continued for another quarter of a century. By 2006,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s investing $1.4 billion a year on clean energy. The alarming fall startled the American scientists, and warning came in 2005 in the form of a landmark report titled “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produced by the top science advisory body, the National Academics, which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boost energy investment written in strong languages by Steven Chu, then the director of th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and now the Secretary of Energy, and Robert Gates, the former C.I.A. director and now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We fear the abruptness with which a lea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be lost—and the difficulty of recovering a lead once lost, if indeed it can be regained at all.”[7]The call was responded by the Congress in 2007 bu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questioned the credibility and dismissed the possible role government can play, the investment rol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should be left to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funding was never allocat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vowed to restore American’s lea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re the input of governmental funding and investment are at a level not seen since the space race. While busy repairing the energy legacy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bama remarked “The nation that leads the world in twenty-first-century clean energy will be the nation that leads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 global economy,” and in his usual charm and charisma, encouraging and assuring for Americans in characteristically Obama style, “I believe America can and must be that nation.” The injection of more than thirty-eight billion dollars into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for renewable energy marke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學生短評精選-陳家慶
*本文為回應12/21葉俊榮教授<氣候變遷與經濟誘因>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只能做不能說與只能說不能做之間──經濟誘因作為政策工具
一、前言
今年12 月21 日,本課程授課教師葉俊榮以「氣候變遷與經濟誘因」為題演講。筆者在過去曾修習過一些經濟系課程,當時將之與政治、法律等學科進行比較,發現其「務實性」性格較為強烈,對於一些爭論往往以「此可為社會帶來最大福利」加以解釋。此一看似「現實」的角度在現今面臨金融風暴與氣候變遷的全球治理當中不斷受到修正或是挑戰。因此,本文將從經濟誘因作為「政策工具」的角度出發,探討台灣政府於全球氣候變遷下的政策抉擇。
二、經濟誘因作為政策工具
在資源配置的利益衝突上,經濟學的研究觸角以經濟的數學模型,在諸多假設下架構出一個可以操作的理論模型。藉此希望達到社會福利的極大化。此一實證性色彩極重的研究途徑,在現實上難免遇到道德上的非難,如「一切以金錢而非價值來衡量」;也被質疑其數理模型是否真能適用到現實生活上;而政治決策的考量也往往不是依照經濟學的模型進行,更為真切的通常是權力的折衝樽俎(當然以經濟學為名進行權力鬥爭的工具又是更複雜的形式)。然而,就現實政策面的考量而言,除了道德正當性的討論之外,我們仍然不可忽略一個政策的「可行性」。美國所發展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即大量使用經濟學工具與思維,如其1936 年「洪水管制法案」(The Flood Control Act of 1936)規定在「計畫對受益人的效益超過可估計成本」的原則下,聯邦政府可以參與防洪計畫[1],並在二戰後逐漸完善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此一決策模式大大降低了政府財政支出,使得政府從納稅人徵得的資源可以獲得更有效的利用。由此觀之,在法律與政策的決定考量當中,「經濟學」雖然在道德上或許會面臨到許多爭議,但在具體客觀的政策可行度上,仍然是非常有用的決策工具。三、國際環境建制的經濟誘因工具現在讓我們把焦點拉回全球環境變遷以及國際環境建制的經濟誘因。在過去幾講當中,我們已經探討過許多經濟誘因工具,如碳排放機制、碳稅等等。這些經濟誘因工具也每每遭到許多團體的抨擊,大多數莫不以其僅是資本主義者的操
作工具或者是「贖罪券」云云。但進一步探討全球環境變遷的特性,我們會發現這些在道德上可以持續爭議下去的工具,在符合其理念預設與條件假設的情況下,卻往往能比口號更能「事實上」對全球環境的維護做出貢獻。
何以見得?
全球氣候變遷是全體人類共同面對的真實事件,同時也是一迅速進行的事件。人類爭取了數百年才得到的自由民主體制,但是環境變遷對於人類可能的傷害卻是非常有可能在一百年內就讓人類文明遭受威脅。因此,這不像以前一樣是一個長久奮鬥的戰爭,我們可以述說無數革命先賢的故事,但是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戰爭,如果我們這幾代沒有獲得明顯的成功,那未來也將無人可以訴說我們對於全球暖化所做出的努力了。正因為此一戰役需要的是明快的決策與法律,也因此以效率還有社會上最大福利為導向的經濟學研究途徑是我們必須要多加運用的工具。以法律、政策為行動綱領以及框架,現時地處理當前的碳排放問題,同時兼顧人類文明的發展。
四、臺灣能源稅課徵風波──只能說不能做?
從前面的討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經濟學工具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事實上的政策效率,然而我們往往要讓施政環境能夠符合其假設,同時在民主社會的要求之下,我們必須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論述以說服社會大眾,不,在此一議題當中,應當是用以說服「世界大眾」。是故,即便國際環境議題往往陳意甚高,但仍就必須面對許多質疑提出它的論述。如何以科學的結果告訴大家自然界的真實情形?如何以具體的法律與政策說服社會大眾接受?這當中又往往牽涉到不同的政商利益與國家衝突。本次哥本哈根會議美中唱雙簧,互相抨擊而到最後發表宣言草
草了事即可看出國際政治的角力仍舊是以國家利益為中心,在討論各種國際議題的時候往往必須調和各種衝突的國家利益,方能在現實環境中遂行其理想。從而,套句大家常常在報紙上看到的話,有些事「只能說不能做」,而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只能說不能做是因為一個在理想上或是經濟預估上應該進行的決策,現實上遇到許多的利益衝突而無法施行;只能做不能說則是因為雖然政策本身符合國家的理性考量,執行上也可以勉強進行,但卻無法產生出一個可以說服社會大眾的論述,因此也只能偷偷摸摸地作,自以為成效出來之後就可以獲得國人諒解。以臺灣前些日子發生的碳稅徵收風波而言,是一個典型的只能說不能做的例子,為了要將能源使用的外部成本加以反映出來,因此需要徵收能源稅,然而,此值世界經濟不景氣(雖然從筆者出生以後台灣的景氣似乎從來沒有好過),工商各界紛紛以為增加成本之政策為萬萬不可為之策,如果貿然實施必將加速台灣產業外移等等原因而大肆反對。我國政府也很識相地否認「真的」要實施能源稅政策,從而將這次的風波壓制下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即便學界對於政策方面有許多的分析,不管是法釋義學的途徑或者是經濟分析的途徑,在面對社會大眾的不同利益之時仍然需要發展更為縝密的論述模式對政策加以包裝、闡明,方能使其真正施行於社會。
五、政策的弔詭──「說一套做一套」的交錯適用?
綜上所述,我們雖然可以知道經濟分析是一個「有用」的工具,但和其他工具一樣,在使用的時候仍然需要考量現實的限制,不管是道德上的非難或者是利益衝突的衡量。也因此,一個施行出來的政策往往是各方利益折衝樽俎的結果,如果與其初衷將比較,往往是「說一套,做一套」。我們過去對這種決策模式往往大加撻伐,但若考量到政府對於調和各方論述能力的缺乏以及自身整合利益的限制,會出現這種模式也是無可厚非的。以蘇花高的興建爭議為例[2],遍面臨了「發展」與「保育」的兩難而拖延許久,最後政府決定「給花蓮人民一條安全的路」,將蘇花高調整為「蘇花改」。沒那麼的發展取向但也犧牲了些許環境考量。如果探究其內容,會發現這也是「發展中心」的思維,只不過力道稍稍減輕了而已,但卻因為其在道路等級還有路線上的讓步,使得「安全」獲得了更高的正當性(與之前的討論相比較),進而使這個議題產生現在的結果。因此,就政策面考量,我們除了利用經濟學工具讓其更有可行性外,對於政策的論述能力也必須強化,或許最後終將落得「說一套做一套」的命運,但至少可以讓政策獲得一定程度的實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郭昱瑩,2007,《成本效益分析》,台北,華泰文化,P.7
[2] 此並非預設「蘇花高」本身就是一個滿足經濟分析的最佳決策,而是要表示一個政策的施行往往不會依照其原先的上位價值加以推動,而是在經過許多次的衝突與調整之後尋求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論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