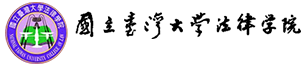按標籤顯示項目: 全球環境政策與法律專題討論
學生短評精選- 萬庭威
*本文為回應12/21葉俊榮教授<氣候變遷與經濟誘因>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揚棄法教條學、擁抱法律經濟分析:方法論上的進步?
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存在衝突?
眾所周知,大陸法系最大的特色在於由羅馬法所派生,並以一部成文法典作為法律的本體。台灣在繼受法律的過程中,主要係受德國法之影響,而德國現代哲學發展之高潮在於自康德之先驗理性論以至於黑格爾的辯證理性論(即一般所稱之德國觀念論),雖說無法斷定哲學思潮對於法學之影響程度,但如此的發展與預設法典中存在先驗價值的觀點非常對味。是故,若法典有其內在的先驗價值,法律人的工作便是開展、發現法律,而不能去創造法律,這即是概念法學之所以形成的基本條件之一。德國後世雖有自由法學派強調法官的自由判斷,但並未形成法學界主流,反而或多或少與法律社會學界更為密切;而概念法學之後的利益法學以及當今位處主流學說的價值法學,更主張將法律的價值置於當事人利益衝突下,法官適用法律應考慮的是如何運用法律將當事人之利益衝突做調和,使個案中的目的性要求衝破法律規則。就此法律思想而言,亦指出法官作為裁判者是如何在當事人利益衝突之間做抉擇,成文法典的角色的只是一個工具箱。這個工具箱雖無法將所有可用的工具都收納進來,但仍可永遠預留一些空位(一般條款),在困難的案件中尋求新的工具以納入法律工具箱。
相較而言,英美法的無法典特性就不會有上述的問題:法官身為法律創造者,在個案中所為之判決並非發現法律,而是更積極地參與當事人間利益衝突的解決。相對的,判決先例原則就有點類似於成文法典的作用,藉由過往經驗與智慧的累積奠定法律基本原則;而一旦法律原則在個案中的實施將造成荒謬的結果,則可用衡平法原則加以補救之,故衡平法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法典中的一般條款。
綜上所述,普通法與大陸法雖然對法律原則的產生想像不同:一則基於無預設的經驗主義立場,另一則偏向先驗理性的肯定;但對於法律人作為決策者,不能無視現實世界的價值衝突這一點立場上並無二致。因此,在台灣的時空背景上若出現死守法教條學的法匠,問題似乎不真的出在學說或是法系不同的問題,而更應該是:在法律繼受的過程中缺乏了什麼要素使得盲從成為一個可行、甚至是大家所偏好的選項,而非仔細開展法律教育與思考的理論面?這個問題似乎不是單純用法律體系上的不同就可以解釋,而更需要其他的方法來考察。
京都議定書裡的經濟誘因到底有沒有用?
在哥本哈根會議以失敗收場,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全球暖化管制新體系看來遙遙無期時,對經濟誘因作為京都議定書主要管制工具進行反省在時機上似乎再恰當不過。京都議定書允許三種彈性機制供各國使用:joint implementation、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以及emission trading,前兩種機制可以產生額外的碳排放權,而多餘的碳排放權則可在emission trading market中自由交易,供有需求者購買。
關於joint implementation以及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所產生的碳排放權於京都議定書中雖要求必須是額外於原狀況的減量,但要如何計算一個JI計畫或是CDM計畫產生的碳權真的是額外,則有許多爭議。除了計算方式本身在科學上已莫衷一是之外,在牽涉開發中國家的CDM機制裡,實踐上還曾有已開發國家到開發中國家進CDM獲得碳權的方式居然是砍掉原有雨林,再重新種樹以便「植樹」這一項名義獲得碳排放權。若缺乏良好的科學計量方法,又沒有強而有力的執行、監督機制,縱令JI及CDM原意是用經濟誘因的方式達到減量的目標,仍然會因為這兩個因素而使得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關於emission trading,在京都議定書中所採的模式屬於baseline and credit交易,而非其他區域性的emission trading market多以cap and trade方式進行。Baseline and credit交易的缺點主要係來自上一段所提及的兩個原因,而無法確保交易的碳權是不是真的已經實質減少排放;而cap and trade理論上雖然只要cap設定好,並嚴格執行之就可以達到減量目的,但在現行的cap and trade機制中,初始的排放量大多用grandfather clause無償給予,而這具有相當大的道德風險:過往污染越是嚴重的公司,在碳交易市場中反而是銀彈最足的,而且這些銀彈還不用花一毛錢就可以取得。此外,在現行區域碳交易機制中的基礎條約裡多具有連結條款,允許其他非同一區域所產生的碳權進入區域碳交易市場,而可能使cap往上漂移,而最終根本沒減量多少。
經濟誘因作為管制手段並非不可行,但在有能源稅、碳稅等等直接處罰排放者、獎勵清潔者的手段可用時,我實在看不出來這些得來極為容易的碳排放權及其交易對於實質減量有什麼幫助,尤其是cap根本漂浮不定、又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情況下,買空賣空的情形只會更加嚴重。
法律經濟分析與經濟誘因:經濟學帝國主義?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界裡似乎以其科學性自豪,不外乎是因為大量的模型建構以及數學的運用。但這樣的自豪轉譯到真實社會中往往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預測失敗。我個人認為問題是出在於數字跟個人、集體行動是兩種不同的範疇,無法相互化約。在數字的隔閡之下,研究者對於真實社會的理解彷彿隔有一層膜,藉由選擇性排除不在模型之外或難以量化卻很重要的變因,我們就看到很多失靈的管制措施在經濟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一點用也沒有,像是京都議定書的彈性機制就是一例。
同理,面對法律研究本身,為什麼經濟分析在方法論上是一種好的工具?難道是因為它運用的數學令人目眩神迷?還是它將各種法律原則化約為理性選擇以為解釋,滿足一套打天下的科學一統論夢想?在批評法教條學的不切實際時,我個人認為解決方式不是急著找另一套唯一方法去打掉它,而應該對法律的本質更加開放地看待,並暫且認為法律是一個獨立的存在,無須急著用理性選擇去化約法律原則。
法律經濟分析確實提供了不同於傳統法學的觀點,並在效率作為一種價值的情形下別具意義。但理性選擇論到底能不能化約其他法律原則,我個人持高度懷疑的立場。同時,經濟學也不是完全數學化的一門學科,然而一般提到法律經濟分析卻不會想到歷史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與方法,這種忽略是有意還是無意,有待進一步的考察。
學生短評精選-洪國華
法律經濟分析目前被認為是不同於傳統之法學方法,有別於採取歷史論、立法論、解釋論的方式,而希望使得在法律適用的判斷上,其結果實質上對於社會有更大的利益,或是使得法律系統的運作可以減少所需的社會成本。法律經濟分析對於傳統法學方法的質疑也正在於是否僅為追求法律解釋邏輯一致性,如在是否違反立法者的本意、擴張解釋或是類推適用等在此多作爭執,而忽略法律適用應考量社會而非社會要按照法律邏輯無矛盾的運轉。
學生短評精選-林季陽
學生短評精選-李新恩
學生短評精選-李崇菱
Recognising the future threats to their survival, Chinese leaders in 2006 embarked and endorsed a new commitment to new energy technology, and boosted funding for research and set targets for installing wind, solar panels, hydroelectric dams, and other renewable sources of energy.[4]In 2008, China became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in the world, and renewable energy alone attracted USD 15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So long as China can ensure a continued growth rate of fifteen percent per annum would ensure that renewable technologies would be equal footing with oil, gas, and coal in the next two decades[5]. China’s President Hu Jintao, declared to the world in October this year China must “seize pre-emptive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energy revolution.” The rate and scale of China’s ambition is astonishing. David Sandalow, the United State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an interview for New Yorker article, remarked on China’s effects in renewable energy is “extraordinary”, and the implication for American, is clear: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makes investments, we are not competitive in the clean-tech sector in the years and decades to come”.
Whe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eenhouse gases emitter, energy policies have gone differently. President Jimmy Carter announced in April of 1977 when America went into the hunt for new energy sources, as result of the second Arab oil embargo, as 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 Public investment in energy research was nearly quadrupled in fund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fortably lead in clean technology by the mid-nineteen-eighties, where more than fifty per cent of the world’s solar cells and ninety per cent of the wind power were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he Regan administration came into power, the deregulation and acting on a pledge to abolish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investment in energy research also were reduced, which continued for another quarter of a century. By 2006,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as investing $1.4 billion a year on clean energy. The alarming fall startled the American scientists, and warning came in 2005 in the form of a landmark report titled “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produced by the top science advisory body, the National Academics, which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boost energy investment written in strong languages by Steven Chu, then the director of the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and now the Secretary of Energy, and Robert Gates, the former C.I.A. director and now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We fear the abruptness with which a lea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be lost—and the difficulty of recovering a lead once lost, if indeed it can be regained at all.”[7]The call was responded by the Congress in 2007 bu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questioned the credibility and dismissed the possible role government can play, the investment role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should be left to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funding was never allocate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vowed to restore American’s lead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re the input of governmental funding and investment are at a level not seen since the space race. While busy repairing the energy legacy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Obama remarked “The nation that leads the world in twenty-first-century clean energy will be the nation that leads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 global economy,” and in his usual charm and charisma, encouraging and assuring for Americans in characteristically Obama style, “I believe America can and must be that nation.” The injection of more than thirty-eight billion dollars into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for renewable energy marke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學生短評精選-陳家慶
*本文為回應12/21葉俊榮教授<氣候變遷與經濟誘因>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只能做不能說與只能說不能做之間──經濟誘因作為政策工具
一、前言
今年12 月21 日,本課程授課教師葉俊榮以「氣候變遷與經濟誘因」為題演講。筆者在過去曾修習過一些經濟系課程,當時將之與政治、法律等學科進行比較,發現其「務實性」性格較為強烈,對於一些爭論往往以「此可為社會帶來最大福利」加以解釋。此一看似「現實」的角度在現今面臨金融風暴與氣候變遷的全球治理當中不斷受到修正或是挑戰。因此,本文將從經濟誘因作為「政策工具」的角度出發,探討台灣政府於全球氣候變遷下的政策抉擇。
二、經濟誘因作為政策工具
在資源配置的利益衝突上,經濟學的研究觸角以經濟的數學模型,在諸多假設下架構出一個可以操作的理論模型。藉此希望達到社會福利的極大化。此一實證性色彩極重的研究途徑,在現實上難免遇到道德上的非難,如「一切以金錢而非價值來衡量」;也被質疑其數理模型是否真能適用到現實生活上;而政治決策的考量也往往不是依照經濟學的模型進行,更為真切的通常是權力的折衝樽俎(當然以經濟學為名進行權力鬥爭的工具又是更複雜的形式)。然而,就現實政策面的考量而言,除了道德正當性的討論之外,我們仍然不可忽略一個政策的「可行性」。美國所發展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即大量使用經濟學工具與思維,如其1936 年「洪水管制法案」(The Flood Control Act of 1936)規定在「計畫對受益人的效益超過可估計成本」的原則下,聯邦政府可以參與防洪計畫[1],並在二戰後逐漸完善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此一決策模式大大降低了政府財政支出,使得政府從納稅人徵得的資源可以獲得更有效的利用。由此觀之,在法律與政策的決定考量當中,「經濟學」雖然在道德上或許會面臨到許多爭議,但在具體客觀的政策可行度上,仍然是非常有用的決策工具。三、國際環境建制的經濟誘因工具現在讓我們把焦點拉回全球環境變遷以及國際環境建制的經濟誘因。在過去幾講當中,我們已經探討過許多經濟誘因工具,如碳排放機制、碳稅等等。這些經濟誘因工具也每每遭到許多團體的抨擊,大多數莫不以其僅是資本主義者的操
作工具或者是「贖罪券」云云。但進一步探討全球環境變遷的特性,我們會發現這些在道德上可以持續爭議下去的工具,在符合其理念預設與條件假設的情況下,卻往往能比口號更能「事實上」對全球環境的維護做出貢獻。
何以見得?
全球氣候變遷是全體人類共同面對的真實事件,同時也是一迅速進行的事件。人類爭取了數百年才得到的自由民主體制,但是環境變遷對於人類可能的傷害卻是非常有可能在一百年內就讓人類文明遭受威脅。因此,這不像以前一樣是一個長久奮鬥的戰爭,我們可以述說無數革命先賢的故事,但是面對全球氣候變遷的戰爭,如果我們這幾代沒有獲得明顯的成功,那未來也將無人可以訴說我們對於全球暖化所做出的努力了。正因為此一戰役需要的是明快的決策與法律,也因此以效率還有社會上最大福利為導向的經濟學研究途徑是我們必須要多加運用的工具。以法律、政策為行動綱領以及框架,現時地處理當前的碳排放問題,同時兼顧人類文明的發展。
四、臺灣能源稅課徵風波──只能說不能做?
從前面的討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經濟學工具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事實上的政策效率,然而我們往往要讓施政環境能夠符合其假設,同時在民主社會的要求之下,我們必須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論述以說服社會大眾,不,在此一議題當中,應當是用以說服「世界大眾」。是故,即便國際環境議題往往陳意甚高,但仍就必須面對許多質疑提出它的論述。如何以科學的結果告訴大家自然界的真實情形?如何以具體的法律與政策說服社會大眾接受?這當中又往往牽涉到不同的政商利益與國家衝突。本次哥本哈根會議美中唱雙簧,互相抨擊而到最後發表宣言草
草了事即可看出國際政治的角力仍舊是以國家利益為中心,在討論各種國際議題的時候往往必須調和各種衝突的國家利益,方能在現實環境中遂行其理想。從而,套句大家常常在報紙上看到的話,有些事「只能說不能做」,而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說」。只能說不能做是因為一個在理想上或是經濟預估上應該進行的決策,現實上遇到許多的利益衝突而無法施行;只能做不能說則是因為雖然政策本身符合國家的理性考量,執行上也可以勉強進行,但卻無法產生出一個可以說服社會大眾的論述,因此也只能偷偷摸摸地作,自以為成效出來之後就可以獲得國人諒解。以臺灣前些日子發生的碳稅徵收風波而言,是一個典型的只能說不能做的例子,為了要將能源使用的外部成本加以反映出來,因此需要徵收能源稅,然而,此值世界經濟不景氣(雖然從筆者出生以後台灣的景氣似乎從來沒有好過),工商各界紛紛以為增加成本之政策為萬萬不可為之策,如果貿然實施必將加速台灣產業外移等等原因而大肆反對。我國政府也很識相地否認「真的」要實施能源稅政策,從而將這次的風波壓制下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即便學界對於政策方面有許多的分析,不管是法釋義學的途徑或者是經濟分析的途徑,在面對社會大眾的不同利益之時仍然需要發展更為縝密的論述模式對政策加以包裝、闡明,方能使其真正施行於社會。
五、政策的弔詭──「說一套做一套」的交錯適用?
綜上所述,我們雖然可以知道經濟分析是一個「有用」的工具,但和其他工具一樣,在使用的時候仍然需要考量現實的限制,不管是道德上的非難或者是利益衝突的衡量。也因此,一個施行出來的政策往往是各方利益折衝樽俎的結果,如果與其初衷將比較,往往是「說一套,做一套」。我們過去對這種決策模式往往大加撻伐,但若考量到政府對於調和各方論述能力的缺乏以及自身整合利益的限制,會出現這種模式也是無可厚非的。以蘇花高的興建爭議為例[2],遍面臨了「發展」與「保育」的兩難而拖延許久,最後政府決定「給花蓮人民一條安全的路」,將蘇花高調整為「蘇花改」。沒那麼的發展取向但也犧牲了些許環境考量。如果探究其內容,會發現這也是「發展中心」的思維,只不過力道稍稍減輕了而已,但卻因為其在道路等級還有路線上的讓步,使得「安全」獲得了更高的正當性(與之前的討論相比較),進而使這個議題產生現在的結果。因此,就政策面考量,我們除了利用經濟學工具讓其更有可行性外,對於政策的論述能力也必須強化,或許最後終將落得「說一套做一套」的命運,但至少可以讓政策獲得一定程度的實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郭昱瑩,2007,《成本效益分析》,台北,華泰文化,P.7
[2] 此並非預設「蘇花高」本身就是一個滿足經濟分析的最佳決策,而是要表示一個政策的施行往往不會依照其原先的上位價值加以推動,而是在經過許多次的衝突與調整之後尋求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論述模式。
學生短評精選-陳家慶
從侵權行為、保險到國家政策
面對氣候變遷的災害補償與風險趨避機制
一、 前言
本次12/7 之演講邀請到台大法律系的老師汪信君前來演講,以”Climate Change, Insurance and Risk Mitigation”為題,講述氣候變遷與環境責任。從氣候變遷帶來的損害討論此方面之侵權責任與保險機制。面對氣候變遷的加速,這些補償、避險工具也面對極大挑戰。於此,我們要問的是,政府的政策在市場上具有這兩種工具的情下,應如何調整以求政策成效的最佳化。
二、 侵權行為的路徑
面對氣候變遷下巨災所帶來的損害,除了就國家行為請求國家賠償外,另一個解決路徑便是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我國民法第184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由此可知,就點型類型來看,負侵權行為者必須要符合損害、故意過失、因果關係等等要件。由巨災所造成的損害而言,其原因往往不會有一個直接的故意加害人或過失加害人,其往往是因為「既有的天災擴大」或是人類的「共業」,從而無法確定因果關係而使請求有所理由。前者如颱風所造成的風災在近幾年隨著氣候變遷而擴大,但我們並無法因此直接向特定人進行求償。即便確認有大量碳排放的廠商應對此負責,如保險業的調查當中發現氣候變遷的與雨量等導致災情的因素有所關聯[1],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確認大量排放的廠商應當就全球增溫導致的天災損害負責,然而進一步的具體的因果關係仍無法確定,更何況如後者所言,全球暖化是全世界人類發展的共業,要如何使特定廠商、單位進行侵權行為的賠償實在有所困難。即便採Proportional Liability,司法攻防所造成的時間、勞力花費,即便使我們獲得實體上的利益,但程序利益往往因此無法顧及,更何況隨著氣候變遷的加劇,若可能每年不斷擴大的農損均循侵權行為路徑求償,那麼程序利益的損害更將嚴重。
三、 保險的路徑
相對之下,保險的路徑對於因果關係的要求較低,風險估算可於事前加以評量,如保險人以公司的龐大財利組織風險與損害調查,各保險人以不同的風險估計提供市場上大眾不同的保險商品以供避險。然而,正由於巨災的風險可能越來越大,風險的評估也將越來越不確定。以莫拉克風災為例,其巨大雨量在事前並無法切確預估。面對這種科學無法事先預估風險,只能事後確定損害的災難,勢必大大降低保險人承保的意願,或是降低願意承保的範圍,此將無法確保人民損害可以確實獲得足夠的填補。例如防洪標準常常以「五十年洪水頻率」、「一百年洪水頻率」來加以估量。就保險而言,或許可以以此量表估算被保險人可能會受到洪水影響的風險。然而,近年來颱風威力擴大,這種洪水頻率已經無法適切表達台灣可能會受到的洪災大小與發生頻率。即便這種量表沒有被巨災影響,但許多事前無法預估的損害也會發生,進而使保險人無法切確預估確實發生的損害或是降低承保意願或保額。例如納莉風災時即有雖然提防沒有被溢堤,但卻因大量降雨使抽水站無用武之地的情形:
養工處長羅俊昇指出,現有市內堤防是兩百年洪水頻率保護,下水道設計標準是五年暴雨頻率的七十八點八公厘;颱風時,因下雨面積大,颱風雨頻率四十五公厘,所以每小時雨量如果超過這標準,下水道容量就會出現積水問題。至於抽水站的排水設計,有的地區因為較高,在暴雨時不用抽水,是採暴雨頻率設計,有的則以颱風雨設計;這次颱風,因為單日雨量和每小時雨量幾乎都超過容量,所以堤防和抽水站無法阻擋都出問題。仔細觀察市區這次淹水原因有兩個,一是洪水溢堤;一是雖未溢堤,但因市區雨量超過部分抽水站的設計容量,造成積水回堵。[2]
因此,雖然保險提供了一個風險趨避的工具,但就政策角度而言,單純的國
家賠償、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保險機制並無法提供一個完善的損害填補機制。
四、 國家政策的抉擇
當然,雖然現行的巨災損害填補機制並無法完整填補損害,但這不代表我們就要拋棄這些模式,全部由國家來進行損害填補。我們要問的是,在現行的損害填補機制下,政府政策可以有如合的回應與調整?因此,以下將從政府的角度去思考,對保險而言,政府是否有足夠的作為增加風險評估的準確程度,以為政府施政參考,同時也可以提供保險業者一個參考評估風險的基準?政府是否可以針對環境高敏感地區,仿照汽車強制責任險的政策,推動強制災害保險?在此當中對於潛在受災戶以及保險業這是否有足夠的誘因?最後,針對政府本身,其是否有辦法在事前的風險防免上進行足夠的風險分擔?當然也不能忽略風險分擔之外政府應該有的是後救助機制,不過這與環境責任的本身就比較沒有直接的關係了。是故以下仍以風險為中心進行政府機致選擇的討論。
1. 風險評估機制的強化
政府本身擁有中央氣象局、環保署等政府機構,並有許多研究組織。這些具有足夠專業知識背景的單位,針對近年來的氣候變遷是否能夠提出一如前述ABI般的估計模型供其他政府機構以及民間業者進行政策或是商品上的調整。這需要政府機關間從風險評估導政策施行的合作協調,以及政府機關以及民間組織的合作,如此方能將科學的數據具體運用到實際的執行面。
2. 強制保險的納入
政府前幾年針對汽車推行了「強制汽車責任險」,降低了車禍等事故因為因果關係而導致損害賠償緩不濟急的問題。而台灣也有許多環境敏感地帶,其中也有些高風險的開發,例如清境農場等等。對此我們可不可以以類似「強制汽車責任險」的「強制環境責任險對在高環境風險地區人民加以保險,使他們在「受災」時也可以獲得一定的補償;而一些高風險的開發也可以因此分擔部分環境責任。
所以我們可以將這種保險分成兩種面向:
1) 針對高環境風險居民的保險,使他們可以在災後受償。
2) 而在高風險地區開發的業者,其短期間內無法搬遷,對其強制投保,使其在因為其開發而產生的損害上由保險進行環境責任的分攤。
由上所知,我們可以發現一些問題,例如環境責任無法確定、保險人承保意願低等等。面對這些問題,我們可以以「不足額保險」因應,不是使保險人全部賠償,而是就可能損害的不同進行非足額的保險或是定額責任險等等。如此一來降低了保險業者可能因災害過大而生的無法預知過大賠償所導致不願意承保的情形。此外,如同強制汽車責任險,其對於保險業者的收入狀並不大,若單獨來看並無法提供保險業者誘因。但保險業者仍願意承保強制汽車責任險,除了國家政策之外,尚因為強制保險可以為保險人帶來客戶,進而有投保其他保險的機會。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強制保險仍然存在誘因,並且可以「部分的」分擔居民以及業者的環境風險。
五、 代結論──政策面的風險分擔
除了風險評估以及保險機制以分擔人民風險之外,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夠確實地於事前預防損害,在災害時能否確實的以國家力量迅速地進行救災,以及災後能否適時提供補償與重建機制都是在討論環境責任時,由政策面應當連同考量的週邊事項。因此,建立一個完整的災害應對機制,整合不同的政府機關以及民間力量是當前氣候變遷下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唯有考量風險評估以及市場機制的運作,方有機會使政策的規劃與執行達到最佳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據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ance, ABI,的調查顯示,氣溫增加攝氏2度,颱風降雨將增加13若是四度、六度則會分別增加,26%及39%。以我國為例,颱風短期間的超大量往往是損超出預期的主要原因。
[2]2001-09-22/聯合晚報/4版/話題新聞
學生短評精選-洪國華
學生短評精選-林季陽
本週演講者為本系汪信君教授,演講之主要內容為介紹巨災保險制度,其中含括可保性、因果關係認定以及國家環境責任等面向。在Q&A時間則另外提及保險制度與其他氣候變遷相關制度如能源稅間之交互。學生則擬在此次之reflection paper中試探討針對氣候變遷的各種制度間可能之發展。
基於損害填補的想法出發,某程度上巨災保險可謂係替氣候變遷這個「因」所造出來的「果」來收拾,然而亦僅得稱為「收拾」而非「善後」,畢竟巨大災害後的重建甚至預防,實難想像純粹的保險制度可能做到此點。因此,若基於風險管理之角度來處理巨災,似乎應該將所有可能以及相關之制度一併加以考慮,方可能建立較具有可行性的氣候變遷避險(climate change hedge)。
事實上營利頭腦動得快的財務金融界,甚早前就已經開始發行巨災債券,針對地震、風災、水災等風險因子,在信託市場、利率市場,藉由信託契約、債券契約以及再保險契約,將對風險之主觀認知差異包裝為具有避險,甚至交易可能性之金融商品。然而追根究底,所謂避險之概念,僅僅是希望從事避險操作之主體得於損害發生時受一定程度之填補,並非如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管制般,具有主觀上積極抑止因氣候變遷所致巨大災害發生此一面向。換言之,此類避險主要仍屬於消極面向。然而,此處所欲主張或謂,值得進一步深入思考的便是,結合積極與消極面向,同時具有管制效果與投資可能性的商品是否有設計可能。亦可能有謂,此種結合經濟誘因之制度現行已有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存在,如果直接就碳交易制度予以改進,是否仍須多此一舉?然學生認為,今日碳交易制度之主要困境便係已過度商品化,除因此易受價格波動影響外,不可諱言的亦可能成為某些有心人士如國際投資客所覬覦的目標,進而忘卻原先欲達成節制溫室氣體排放、緩和氣候變遷之初衷。因此縱使原先設計出碳交易制度之立意良好,亦無法否認現實存在的這些面向。
是故,學生認為可能引入投資組合(portfolio)之概念,來結合自本課程自開學至今,由演講者、報告同學們所曾介紹過的種種制度。從能源稅、碳交易、總量管制、環境影響評估與放款標準、巨災保險,再加上現行財金市場上亦有一定程度發展之巨災債券(Catastrophe bond, Cat bond)與巨災選擇權、巨災期貨、巨災交換契約(Catastrophe swap contract)等衍生性商品。例如,於報酬率觀念上則可能選擇以減少排放量百分之幾,較類似總量管制之概念,但在商品內容中則給予投資人(可能是一般投資人、跨國企業甚至國家單位)上述制度之組合,依投資人需求來加以設計。換言之,即係欲由此種組合,一方面降低巨災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投機面向,另一方面也不致過度偏離經濟誘因。對於風險愛好者(risk lover)以及風險趨避者(risk averse)均得選擇其所偏好之氣候變遷管理制度。然而亦不得不承認,此種思考仍有其現實層面上窒礙難行之處。
首先,是在於投資報酬率觀念之設定,減量排放的目標對甚多不具環保意識或將其擺在次要地位的商業界人士來說,仍屬不切實際的道德層次呼籲,說難聽點就是達成環保目標、減量排放若無法化為貨幣價值,縱然有再多好處,也不容易進入其策略思考之範圍之中。如何在兩種邏輯、語言中切換以達成溝通效果,實非易事。
其次,則是商品內容之設計本身便屬嚴苛之任務。常見之債券、選擇權等,其定價模式中所考慮之種種變數均屬於量化指標,制度中屬於質化之部分如何納入定價模型中,也是一大問題。
最後,若牽涉到跨國企業或國家責任,尚有需要與當地法規接軌的問題,甚至還需考慮到與國際條約等之交互關係。是以上述幾大問題,仍屬需要進一步思考,方可能使風險管理角度下的氣候變遷投資組合實現。
學生短評精選-辛年豐
以往當我們面對環境損害時,多有以保險制度做為管制手段,也發揮了一定的功能[1]。然而,這樣的制度是否足以使用到氣候變遷所生損害之中,還有待討論。有關以保險填補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損害,有兩組基本概念必須加以理解。從這兩組不同的概念下,可排列組合出不同的保險制度設計,並本於此等排列組合進行一步討論制度設計的可行性。
所謂「責任模式」,是指保險人及要保人成立保險契約之後,一旦保險事故發生而有給付保險金之必要時,須以民事上的侵權行為法為基礎,惟有存在有對保險事故發生必須負責的人,保險人才有負保險金的責任。反之,「補償模式」則不以民事上的侵權行為責任存在為基礎,旨在對保險事故對要保人所造成的損害進行填補,因此,只要保險事故發生,保險人即有給付保險金的義務。
所謂的「強制保險」,是指對於保險契約的締結,當事人並沒有自我決定的空間,而採取強制締約的方式,要求法律所指涉的當事人必須繳交一定的保費,以使國家所定達成的公行政任務可以達成。此由於涉及對人民締約自由的限制,因此,如採用此等模式,應以具有法規範基礎為必要。反之,「任意保險」則完全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主,只有在當事人具有締結保險契約之意思時,才會成立保險契約。一般保險法上的保險契約多屬此種類型。
在方案的選擇上,如前所述,由於氣候變遷所生損害的責任不明,每一個排放溫室氣體的行為人對遭受損害之人,所要負的責任究竟多少,在科學上也並非可以截然加以區分的。是以,要以清楚定位當事人責任為前提的「責任模式」,加以處理氣候變遷所生損害的問題,將有先天上的困難。從而,要以強制的責任模式及任意的責任模式兩者處理此等損害的問題,在現階段而言,可行性也將大為降低。
既然以責任模式加以處理氣候變遷所生巨災的問題有其侷限,則所剩的解決途徑,即剩下強制補償模式的保險及任意補償模式的保險兩者。如採用任意補償保險,則必須考慮到保險實務上,能有能力投保的人,通常為衣食無虞的中產階級。然而,從實際受災災民的經濟能力加以觀察,可以發現實際上受有損害者,多屬居住於偏遠山區、低窪等環境敏感地區之人。這些人平時可能在照顧三餐的成問題了,更遑論要另外撥出一部分的財富投保,是以,我們可以發現採用此等模式先天上即忽視了一部分人的生計,而使實際上最需要受到照顧的人們無法在國家法制的設計下得到最基本的照顧。也因此,此等方案實際上的可行性也就大為降低了。
另一方面,在制度上採用強制補償保險的模式以為配套,或許可以期待兼顧在管制上行政成本的花費及被害人所受損害的填補。但實際上,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卻是究竟那些人可以成為強制的對象,如果所強制的對象僅限於是具有財力的產業,則如前所述,真正需要受到幫忙的災民同樣無法有效地納入國家法體系之中有效的保護。但如果強制的對象擴及全民,雖然表面上可以讓所有的人都納入成為損害填補的對象,但必須注意的是,保險費的收取必須符合實質平等的要求。其情形正如目前全民健保制度的實行,在我國雖不能說運作得百分之百的完美無瑕,但至少已有一定的經驗,或許是比較可以期待的制度。只是,實際上是否可行?有待本文繼續進行討論。
如前所述,欲以保險制度填補氣候變遷所生損害,當以將全民納入保險對象,並採強制的填補模式較為可行。然必須注意的是,氣候變遷所生的損害具有風險巨大、不確定性及相互牽連等特色,是以在保險市場下要有良好的計算及精準的定價是相當複雜的,也增加了保險運作的困難性[2]。當前,我們所可確定的,是氣候變遷會帶給人類損害的「危險」;但這個危險究竟會帶來何等規模的損失,所影響的人民究竟有多少等,都還是我們所無法確定的「風險」。對於風險的預估,在相關資訊尚未清楚的今天,保險人要加以預測並計算所可能支出的保險金,並本此計算所要收取的保險費,在實際的運作下,都具有一定的困難。實則,在資本市場的運作之下,當保險商品的販售無法帶給保險人一定的利益,要讓民間的保險人願意承保的可能性也將會相當的低。如此一來,又降低了強制填補模式保險的可行性。
又保險制度本身也要注意到保險公司自我風險的分配,是以多會輔以再保險,及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且再保險的公司與金融商品的販售在商業全球化的今天,勢必也不得不與其他國家的業者及投資人有所連動,如何顧及跨國及本國之保險業本身及商品安全性的監督,相信也將是制度設計上的一大挑戰[3]。在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對金融管制都不見得可以有效因應,而釀成全球金融巨大損害的今天,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開辦這樣的保險,可能造成人民除了要承擔具大的環境風險之外,還要進一步承擔不可預估的投資風險。同時,當損害過大而非當時保險費率精算時所可預料時,要保人的損害也可能無法得到有效的填補。凡此,都是我們在思考保險可行性時所必須一併加以考量的。
由於氣候變遷帶給人民的是無法預測的大幅損失,而在現制下,要完美地以保險及侵權行為法解決此等問題,照顧人民最為基本的生活也存有制度上的困難。因此,我們即須思考如何對人民做有意義的制度設計,以因應可能到來的環境巨災。
近年來,為了追求行政任務履行的效率,許多國家都對其國家任務進行縮減,提倡「合作國家」[4]的理念,將許多的公行政任務交給民間執行。然而,實際上,民間所願意接手並執行者,多是因為認為此等事務對其有利可圖,如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利益,而只能「做功德」而已,許多民間企業就會選擇袖手旁觀。本來法學理論的推展,與時代的需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在我們面對氣候變遷問題,依既有的法制度及理論無法有效解決時,即有重新加以思考的必要。當代許多環境問題確實對國家任務所著根本性的衝擊,我們可以知道,國家存在的目的,即在照顧人民的基本生活。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確定,我們所需要的國家,是一個可以「主動多做事」而非「冷眼旁觀,凡事以國家任務縮減而踢皮球」的國家,當人民面對巨大的災難時,國家應擔保人民的基本生存,並對此負最終局的責任,否則國家的存在將失其正當性[5]。本於這樣的體認,在法制度上也當有進一步的因應之道,包括「嚴肅思考如何解決以往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下,所造成貧富不均的問題,包括思考使用環境公課及能源稅等管制手段」、「國家財政收入的公平性,並從稅收中確保國家有足夠的財力對環境災民進行照顧」、「對於環境敏感地區投注更多資源,從預防原則的角度思考,實質上因應未來幾年可能到來的損害」等。都是對國家任務再轉型後,國家所可以進一步履行其任務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