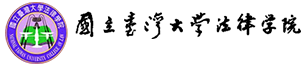按標籤顯示項目: 全球環境政策與法律專題討論
週四, 13 六月 2024 22:12
2009年11月2日課程內容 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舊公約與新挑戰--氣候變遷下國際生態保育公約的調整與回應
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
舊公約與新挑戰--氣候變遷下國際生態保育公約的調整與回應
葉俊榮/張文貞 課堂演講
呂尚雲/曾燕倫 整理
2009.11.2
壹、氣候變遷下生態保育與政策之互動
全球氣候變遷不只影響人類的生活,在全球暖化日趨嚴重的今日,許多生活在各地的自然物種已飽受威脅。最明顯之例,即為居住在極地的北極熊。由於全球暖化、冰山融化,北極熊的棲地快速消失,熊群們的健康狀況也隨之惡化。然而,冰帽融化、棲地喪失、物種滅絕的問題不只是生命科學界關切的議題,其更連帶牽動民主國家政治局勢的發展。例如,在美國,環保團體與政治人物對於北極熊是否要列入聯邦〈瀕臨滅絕物種法〉中加以保育,就引發了強烈的爭辯,甚至引發後續的政治效應,背後更牽涉到美國共和黨對於支持阿拉斯加油田開採的政策利益。
有趣的是,北極熊的保育除了在上述例子中造成美國政治、聯邦各州政策的激盪與爭辯外,科學界竟也出現歧見。當地伊努特族人和部分科學家認為近年來環保意識的高漲和環境保育工作的實踐,事實上已經使北極熊的數目增加,根本不需再特別保育熊群。對北極熊列入保育物種在美國引起之訴訟或是政策辯論,是否會因為科學證據的改變而有完全不同的結論,亦值得持續觀察。事實上,法律或政策如何回應不斷變遷的環境或科學知識,是環境或科技相關法律或政策典型的挑戰,兩者間也應該建立更好的連結與回饋機制,才可能發展出有效因應當今受氣候變遷重大影響之相關環境或生態國際規範機制。
貳、國際生態保育公約面臨氣候變遷議題之挑戰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保育在氣候變遷議題受矚目前,已有相當多的討論,並有許多國際公約做為規範基礎。1993年生效的生物多樣性公約有三大原則:1)生物多樣性的保育; 2)永續利用; 3)生物資源利益的公平合理分享。其中生物資源的公平與合理分享可以說是此一公約最重要的原則。公約一方面讓各個國家基於主權來享有其生物資源,但另一方面同時要求各國必須允許其他人得以公平合理地接近使用,任何植基於這些生物資源所得的科技研究成果或智慧財產權,均必須為所有人類,尤其是擁有這些生物資源的國家及人民所共同分享。在過去,許多大型藥廠到巴西蒐取珍貴雨林植物做成抗癌新藥,卻又以極高的價格賣回當地市場,完全未考慮生物資源使用的公平和正義,類此情況就是生物多樣性公約所欲避免的。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氣候、地理位置以及環境造就了許多獨一無二的生物,因此在生物基因資源上占有很強的優勢,這在主權國家擁有生物資源的前提下非常有利,我們應設法利用。
值得進一步省思的是,這些公約的基本原則是否足以因應氣候變遷在物種、生態及環境上所產生的各種新興議題?在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更多生態或是自然環境面臨巨大的威脅,例如珊瑚、環境敏感地區、沙漠、和濕地。先舉濕地為例,濕地具有低窪、鄰近海洋的特質,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海岸線快速後退,因此造成濕地面積大量減少,連帶使居於其中的生物面臨流離失所的困境。而棲地的喪失也是嚴重影響生物多樣性消失的主因,棲地的破壞、汙染和零碎化,都使賴以維生的生物無法繼續生存。棲地消失的問題在台灣原本就特別嚴重,原因在於我們是地質敏感、面積狹小卻又為眾多亞種生物聚集之處,建設公路或輸油管所帶來棲地零碎化的負面影響格外重大。在氣候變遷的衝擊之下,地貌快速改變、土石流日趨頻繁,遷徙鳥類的生存空間也被壓縮。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黑面琵鷺,黑面琵鷺為瀕臨絕種的保育鳥類,全世界大約有一半的東北亞黑面琵鷺在冬季南遷時,會停留於台灣曾文溪口的七股濕地,氣候變遷導致海岸線後退、濕地消失,使其在台灣喪失重要的中繼休息站,連帶影響其南遷的時程、破壞生物的生理時鐘,黑面琵鷺因此面臨更快速滅絕的危機。面對這些氣候變遷下的新興議題,生物多樣性公約的機制足以反應與處理?其又應如何與其他國際公約配合、接軌?或是必須重啟另外的程序來做反應?凡此均亟待我們更深入的進一步思考並提出法律與政策上的回應。
参、既有之國際生態保育公約的相關機制仍不足以回應氣候變遷的影響
在反省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同時,我們可以回到前述北極熊的例子,作進一步的思考。北極熊棲地喪失的問題,當然不只是美國的開發行為或是任何單一因素所造成,背後牽涉到全球暖化與各國共同責任的問題。對於這些涉及共同連帶以及大尺度的氣候變遷議題,我們如何從目前的法律或政策機制來作適切回應?環境保護公約緣起於六零年代,當時的公約仍然尊重國家主權、信賴科學與協商機制。但是這些區域性、以國家為中心的公約在氣候變遷下已經不足以前述這種處理大尺度的連帶責任問題。
同樣的困境也曾出現於國際人權的發展歷程中,這也使得人權公約在晚近所發展出的問題解決機制或許可以作為參考。國際人權與環境議題的交界面,可從很多人提到的沙漠化談起。許多非洲國家缺乏水和食物,有時已達到威脅生命、健康的程度,在國際人權法上,利用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簡稱ICESCR)的機制,從原本公約第十一條享有食物、免於飢餓的權利,發展出人民享有乾淨用水的權利,權利主張對象更因此從當地政府、內國、延伸擴及到外國以及國際組織等。換言之,如果人權已經是跨越國境的普世價值,且有國際訴訟的機制可供使用,氣候變遷所帶來大尺度規模的破壞,是否也應以類似國際人權公約問題處理機制等大尺度的方式回應?尤其是在現行ICESCR的訴訟方法下,以全球共同的人權價值做為基礎,去主張環境、水、食物鏈結的破壞所造成之人權侵害,是否更能完整且迅速的回應全球氣候變遷下急迫的生態滅絕問題?近來國際人權公約中已經打破國家主權疆界,但環境生態保育公約仍然侷限、聚焦在每個國家對於生物資源的利用,未能掌握問題的重點,遑論發展出一套具體可行的解決機制。
當然,面臨氣候變遷這樣大尺度的問題,所面臨的挑戰不僅於主權國家的疆界或生物資源利益的獨占或分享,更多是涉及氣候變遷與其影響的連結中所產生複雜的生物、生態、政治、經濟等相關問題。在前述美國環境團體保育北極熊的例子中,環境保育團體僅討論各種利益團體的衝突,希望利用將北極熊列入保育動物的方法來緩解物種消失的問題。不過,物種消失的背後,隱藏的是棲地破壞、等全球暖化等全球連帶責任的問題,在北極熊的例子中,這部分卻鮮少被凸顯及深入反省。又如台灣的濕地,今天在全球暖化、海水上升的威脅下,已經不同於過去只要停止人為開發就能解決濕地遭破壞的問題,大尺度、跨國的氣候影響超越了國家所能控制的範圍。這些都顯示暖化所帶來的物種滅絕、冰山融化等等現象,法律政策決定者很難判斷應以何種方法、在何時介入,也因此在生態保育的面向下,氣候變遷將為全球生態保育帶來更大的挑戰,並需要投入深切的思考、發展靈活多元的機制始能有效解決問題。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週四, 13 六月 2024 22:11
學生短評精選-黃如璟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能源、碳與地球人的世界 B96A01014法學三黃如璟
A. 節能VS減碳?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課本上就寫說再過五十年,能源就會被消耗殆盡。現在,我想你們的教科書上應該還是這樣寫著,『再過五十年,能源就會被耗盡』,你看因為人類一直不斷地尋找新的能源……」蕭院長說著。這時的我,腦中不禁想起幾個畫面:曾經看過的一部紀錄片,那是關於台大學生組隊到澳洲參加太陽能賽車大賽。在片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各個專精的好手們,都卯足了勁,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最省能的技術、設計最輕巧地太陽能車。賽程中,他們每日都要精準計算出可以吸收最多太陽能的時刻出發,並在沿途忍受著澳洲特有的蚊蠅騷擾、熾熱難耐的高溫,以及一整天待在特殊而非人體工學的座椅上。
在長江三峽大壩的興建中,我去過了一次,我驚嘆於中國大陸為了養活那上億的人口,為了生產全世界的食衣住行、為了成為世界金融老大,所做的犧牲。所犧牲的是千年古蹟、中華文化的遺跡、還有成千上萬被迫離開老家、被逼著遷村的居民。
不論那些經濟學者、科學家、政治人物在國際會議上對於「節能減碳」這四自政策如何詮釋,從太陽能賽車手的汗流浹背、長江三峽淹沒的古都……,都可察覺到,雖然過了五十年人類還有能源可用,人類總還可以找出新的替代能源,但那過程總是非常艱辛的、是耗時的、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所謂的新科技、新技術都是個未知數。
因此當院長最後說「節能優先於減碳」時,我深表贊同。因為一旦明白能源的取得在未來只會更加不易時,就不難理解蕭院長所謂「節能」的重要性了。尤其在能源依存度接近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大部分的能源都是靠進口而來時。另一方面如果未減碳而過度地消耗能源,豈不是使得。
B. Carbon Tax VS Cab and Trade?
從綠色稅制改革到碳交易市場,蕭院長主張台灣應先徵收碳稅,也就是能源稅,當管理機關取得足夠的相關資料,知道大約各個產業、不同區域碳的排放量後再漸進式的採行現在某些已開發國家中已在採行的碳交易市場。
根據蕭院長的分析,台灣現行碳稅制度,一方面反映代際間的外部性(intergenerational externality),也就是使用者成本,由於大多數能源屬於不可再生的耗竭性資源,這一代的使用量會影響下一代的使用量;而另一方面則反映在人類使用能源對於環境所造成的損害。除此之外,它還能夠達到至少雙重紅利的好處,第一為促進環境保護、能源的節約利用;另一則為財政中立原則。
C. 碳稅的訂定
今天蕭院長演講中提到對於碳稅的訂定,其實一個bargaining的過程,覺得很有意思,因此在今天聽完演講後,特地上網查了相關的資料,很好奇台灣還有世界各地相關政策的發展狀況。
碰巧的是,就在今年四月二十八日,高雄才剛通過「碳稅徵收自治條例」,條文中規定,「本市境內經營營利事業,每年排放二氧化碳1萬公噸以上者,都應向稽徵機關申報繳納碳稅;由於碳稅屬於特別稅,課徵年限為4年。條例訂定的稅率為每年排放200萬噸者,每公噸課徵50元,超過200萬噸者採累進稅率,最高每年課徵7億元。」根據新聞指出,該條例施行,高市每年可增加28.8億元稅收,包括中鋼、中油、台電就佔了28億元。
可見得高雄市就是以二氧化碳排放量來課稅的,超過一定額度的二氧化碳就累進。另外其他國家的做法,則是以化石源料為燃料所產生的CO2排放量為課稅的稅基,以各種能源的「含碳量」之多寡來決定稅率,含碳量高的能源課以較高的稅率。他的好處在於除了可以減二氧化碳的排放,更可以課稅的手段,增加高含碳量能源的使用成本,透過價格機能來減少高含碳量能源的使用量。
D. 中央vs地方
目前台灣包括花蓮縣、雲林縣都已制定碳稅課徵自治條例,但中央政府財政部、經濟部反對,至今均無法施行。這是目前國內的情形。有趣的情況是,若從世界(聯合國)政策的角度來看,也出現了「地方想要,中央猶豫」的情形。
ICLEI(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全世界最大的城市聯盟,台北縣市和高雄市有加入),才在上個月在波瀾的波茲南召開,還故意挑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隔壁開,目的就是要對聯合國施壓,要求聯合國會議協談代表,就爭議事項儘快做出協定。所謂地方勢力,就是以「城市」做為減碳的主體,他們主要是以減量為目標。但是同樣的,並不是強制規範。
除了減量,最令人驚奇的是英國的例子,由於英國政府是在2010年開始,只要超過一定使用量便徵收碳稅,因此有NGO便邀請34個地方政府,一起試行模擬碳交易,以強制減碳5%,未達成者要像其他城市買排放權。而碳價是由市場喊價來達成的。英國的做法和蕭院長所提倡的先徵碳稅,再逐步朝向碳交易市場比較起來似乎很不一樣,不過因為有許多細節技術上的操作和概念是不相同的,我並未仔細比較。
上述的資料正好可以和蕭院長的演講呼應,「集體決策的制定相當困難,尤其當政治的力量又很大的時候。」的確,若要建立一套完整的體制,中央的腳色是沉重的,畢竟每一個決策都會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台灣,占世界總排放量高達1%(三億噸),全球排放量高達22名;然而無論在總人口、世界面積相較之下,卻又顯得如此渺小。在短短的一年內,台灣飽受天災的威脅,多半與氣候變遷也有絕大的關聯,縱然台灣不在受管制地國家之列,然而若要使台灣環境不至過於脆弱,便是要以國際環保工作為責任,並將其列為國家長期的環保政策的首要項目才是上策。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週四, 13 六月 2024 22:04
學生短評精選-黃麗竹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我國施行碳稅可能產生問題之探討
科法一 r98a41027 黃麗竹
前言
「綠稅」是這次演講中蕭院長極力主張的政策。而綠稅中的「碳稅」,與「碳排放交易」兩制度,在環保意識覺醒的現今,皆為世界許多國家實施節能減碳政策重要的工具。惟兩種制度各有其擁護者,何者最適,至今爭論不休。
蕭院長極有創見地提出了「碳稅先行10年,碳排放交易後行」的策略。其依據Weitzman定理來說明「短期應以稅為減量工具,長期以總量管制為工具,以降低經濟效率損失」。如此的作法,以經濟模型來看,相當有說服力;不過實際上的運作,不可能總是像模型一般順利。雖然原則上我贊成這項策略,但是關於碳稅,仍有以下幾點疑慮。
對碳稅的質疑
1. 能源稅、環境稅與碳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
演講過程中,院長多次交替使用能源稅、碳稅等名詞,讓人有些困惑。直到後來才說明了其將之分為「能源稅」及「環境稅」兩大架構。但由此引發了疑問:將「碳稅」(即對CO2排放量課稅)置於「環境稅」之下,而院長又說對使用能源課稅其實就等於對溫室氣體課稅,如此一來,不是有對同一客體重複課稅之嫌?
2. 課稅對於碳排放減量真的有效?
施行能源稅,能源價格提高,除了主要能夠降低人們使用能源的誘因外,確實
能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但此為「間接」而非直接的效果,對於減碳的「量」力道是否足夠,值得探討。如果說能源稅主要功能本來就是「節能」,「減碳」則須由碳稅來實現,但其實效果還相當不確定的。因為碳稅從價格面而非數量面來管制。蕭院長說「課稅事實上就等於無限制出售排放權」,那這豈不表示雖然廠商有經濟誘因減少碳排放量,但如果對其來說排放所獲得的利益大於繳稅的不利益,則課稅的結果還是無法像碳交易一樣來的明確?
3. 討價還價而來的最適稅率?
演講後的課堂討論中,蕭院長坦承,其實所謂每公斤課的碳稅價格都是依靠「bargaining」而來的。最適稅率無法單純從經濟模型中知,因此需要政府與其他民間團體部門協商;而每個人提出的稅率不但不會相同,還都會各具理由。例如蕭院長剛開始提出極高的每公斤兩千元價格,目前降到一千,而在〈經濟衡論〉(2008.10)專訪宏仁集團總裁王文洋文章中提到他以IPCC資料每公斤20~50美金為依據,認為台灣應先從10美金開始課徵再逐年往上調整。由此可看出稅額協商可能面臨各執一詞的情況,遑論背後還可能有利益團體因利益分配而操弄的問題。
4. 對誰、對什麼課碳稅
這也是令我相當困惑的一點。蕭院長的簡報中(碳排放交易機制建置之研究期末報告98.9.25 p.41)提及碳稅徵稅對象「全面」,是指工業部門而言又或是全國人民大小商家?如果是連住家單位都課徵碳稅,那麼是以何種標的為課徵的目標呢?住家的碳排放量如何測量?將之加諸於水電費之上?
又如果只將碳稅限定施行於產業界,會不會是一種不公平呢?產業界各廠商的碳排放量又是如何測定?抑或是非用測定碳排放量方法而是直接將碳稅加諸於所產出商品之上,那進出口產品是否應課徵?會不會與別國重複課徵?
5. 實際實行的困難
除了制度面設計有其困難外,實際施行時也有其問題。首先在申報方面,蕭院長說「誠實申報」,有助於課稅資料的建立,並於其簡報中也肯認如此能為將來碳交易市場資料之前導。但從屢屢被揭露的逃漏稅弊案可知,利益往往引發逃漏稅,何況是碳稅如此龐大之金額?
再者,相較於碳排放市場能自由交易排放量,碳稅強制加諸於所有廠商之上,容易引起反彈。最令人掙扎的,就是上課同學們對於碳稅可能造成廠商被迫轉型甚或因而倒閉引發失業潮的問題。我國憲法明文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生命權,所以我認為一定要有完整配套措施保護其權益才可施行。
另外,雖然目前我國似乎不承認所謂「環境權」的概念,但根據憲法第22條以及目前國際對環境問題日益關切之發展趨勢,環境權將來極可能成為人民之重要權利。那麼,有人有可能據此對政府請求,或對抗廠商,權利衝突發生時,孰輕孰重?
結論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的公平性,以及其可能帶來之多重紅利,碳稅施行的願景相當吸引人。相對於目前我國國內碳交易市場太小,而如何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尚未建立,也需長久時間才能建立。因此我贊同蕭院長碳稅先行的政策,但不能因此忽略上述問題,必須儘量建立完善配套措施防範之。
另外,除了關注產業界的節能減碳,其他如住家、學校等地方也應納入考慮,但是我認為以課稅以外方式應較為可行。以自身為例,現在住宿的地方是以購買電力卡的方式計算電費,且一度電價錢3.7元,為住家用電相當高的層級,因此用電習慣和以往住校內宿舍真的大不相同。基於「使用者付費原理」,調高電價或省電折扣應該能夠達到使民眾節約使用能源的效果。
參考資料:
http://www.tri.org.tw/oil/file/article22-971029.pdf 能源稅碳稅及碳權交易制之整合 梁啟源
http://www.cepd.gov.tw/att/files/200810%E7%89%B9%E5%88%A5%E5%A0%B1%E5%B0%8E%E7%B3%BB%E5%88%97%E4%B8%89.pdf 台灣經濟衡論2008.10 vol.6 no. 10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週四, 13 六月 2024 22:04
學生短評精選-黃麗竹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我國施行碳稅可能產生問題之探討
科法一 r98a41027 黃麗竹
前言
「綠稅」是這次演講中蕭院長極力主張的政策。而綠稅中的「碳稅」,與「碳排放交易」兩制度,在環保意識覺醒的現今,皆為世界許多國家實施節能減碳政策重要的工具。惟兩種制度各有其擁護者,何者最適,至今爭論不休。
蕭院長極有創見地提出了「碳稅先行10年,碳排放交易後行」的策略。其依據Weitzman定理來說明「短期應以稅為減量工具,長期以總量管制為工具,以降低經濟效率損失」。如此的作法,以經濟模型來看,相當有說服力;不過實際上的運作,不可能總是像模型一般順利。雖然原則上我贊成這項策略,但是關於碳稅,仍有以下幾點疑慮。
對碳稅的質疑
1. 能源稅、環境稅與碳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
演講過程中,院長多次交替使用能源稅、碳稅等名詞,讓人有些困惑。直到後來才說明了其將之分為「能源稅」及「環境稅」兩大架構。但由此引發了疑問:將「碳稅」(即對CO2排放量課稅)置於「環境稅」之下,而院長又說對使用能源課稅其實就等於對溫室氣體課稅,如此一來,不是有對同一客體重複課稅之嫌?
2. 課稅對於碳排放減量真的有效?
施行能源稅,能源價格提高,除了主要能夠降低人們使用能源的誘因外,確實
能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但此為「間接」而非直接的效果,對於減碳的「量」力道是否足夠,值得探討。如果說能源稅主要功能本來就是「節能」,「減碳」則須由碳稅來實現,但其實效果還相當不確定的。因為碳稅從價格面而非數量面來管制。蕭院長說「課稅事實上就等於無限制出售排放權」,那這豈不表示雖然廠商有經濟誘因減少碳排放量,但如果對其來說排放所獲得的利益大於繳稅的不利益,則課稅的結果還是無法像碳交易一樣來的明確?
3. 討價還價而來的最適稅率?
演講後的課堂討論中,蕭院長坦承,其實所謂每公斤課的碳稅價格都是依靠「bargaining」而來的。最適稅率無法單純從經濟模型中知,因此需要政府與其他民間團體部門協商;而每個人提出的稅率不但不會相同,還都會各具理由。例如蕭院長剛開始提出極高的每公斤兩千元價格,目前降到一千,而在〈經濟衡論〉(2008.10)專訪宏仁集團總裁王文洋文章中提到他以IPCC資料每公斤20~50美金為依據,認為台灣應先從10美金開始課徵再逐年往上調整。由此可看出稅額協商可能面臨各執一詞的情況,遑論背後還可能有利益團體因利益分配而操弄的問題。
4. 對誰、對什麼課碳稅
這也是令我相當困惑的一點。蕭院長的簡報中(碳排放交易機制建置之研究期末報告98.9.25 p.41)提及碳稅徵稅對象「全面」,是指工業部門而言又或是全國人民大小商家?如果是連住家單位都課徵碳稅,那麼是以何種標的為課徵的目標呢?住家的碳排放量如何測量?將之加諸於水電費之上?
又如果只將碳稅限定施行於產業界,會不會是一種不公平呢?產業界各廠商的碳排放量又是如何測定?抑或是非用測定碳排放量方法而是直接將碳稅加諸於所產出商品之上,那進出口產品是否應課徵?會不會與別國重複課徵?
5. 實際實行的困難
除了制度面設計有其困難外,實際施行時也有其問題。首先在申報方面,蕭院長說「誠實申報」,有助於課稅資料的建立,並於其簡報中也肯認如此能為將來碳交易市場資料之前導。但從屢屢被揭露的逃漏稅弊案可知,利益往往引發逃漏稅,何況是碳稅如此龐大之金額?
再者,相較於碳排放市場能自由交易排放量,碳稅強制加諸於所有廠商之上,容易引起反彈。最令人掙扎的,就是上課同學們對於碳稅可能造成廠商被迫轉型甚或因而倒閉引發失業潮的問題。我國憲法明文保障人民財產權及生命權,所以我認為一定要有完整配套措施保護其權益才可施行。
另外,雖然目前我國似乎不承認所謂「環境權」的概念,但根據憲法第22條以及目前國際對環境問題日益關切之發展趨勢,環境權將來極可能成為人民之重要權利。那麼,有人有可能據此對政府請求,或對抗廠商,權利衝突發生時,孰輕孰重?
結論
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的公平性,以及其可能帶來之多重紅利,碳稅施行的願景相當吸引人。相對於目前我國國內碳交易市場太小,而如何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尚未建立,也需長久時間才能建立。因此我贊同蕭院長碳稅先行的政策,但不能因此忽略上述問題,必須儘量建立完善配套措施防範之。
另外,除了關注產業界的節能減碳,其他如住家、學校等地方也應納入考慮,但是我認為以課稅以外方式應較為可行。以自身為例,現在住宿的地方是以購買電力卡的方式計算電費,且一度電價錢3.7元,為住家用電相當高的層級,因此用電習慣和以往住校內宿舍真的大不相同。基於「使用者付費原理」,調高電價或省電折扣應該能夠達到使民眾節約使用能源的效果。
參考資料:
http://www.tri.org.tw/oil/file/article22-971029.pdf 能源稅碳稅及碳權交易制之整合 梁啟源
http://www.cepd.gov.tw/att/files/200810%E7%89%B9%E5%88%A5%E5%A0%B1%E5%B0%8E%E7%B3%BB%E5%88%97%E4%B8%89.pdf 台灣經濟衡論2008.10 vol.6 no. 10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週四, 13 六月 2024 22:03
學生短評精選-洪國華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探索生質能源的第二條路:農業廢棄物與基因改良作物的重新定位》
全球環境政策與法律專題討論
Reflection Paper B94B01078 生命科學四 洪國華
能源(Energy),此一事物可以說是維繫我們生命現象不可或缺的存在,舉凡所有的生命現象代謝、生長、生殖、感應和演化均是建立在生物本身可以自周圍獲取能源的基礎上;而社會活動當然也是如此,從最基層的生產活動到最後的消費活動,也一樣是一個能源傳遞的過程,由此可見能源對於現代社會之重要性,能源的取得變成主宰一國發展的關鍵。
就我們能夠利用的能源而言,化石能源可以說是我們人類最大的能源來源,但是一直以來,
以我國的自然環境和其他先天條件而言,高達97.8%的能源依賴進口[1],一旦在能源進口這方面受到國際政治或是其他因素的影響,或是國際能源市場大幅波動的情況下,勢必會對於國內民生經濟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為此我們也當然要重視如何能從對於能源進口或是根本就要從化石能源的依存上解脫出來,為此生質能源本身或許也可以算是一個發展的空間。
固有生質能源作物並非我國可以主要仰賴的對象
世界上絕大多數發展生質能源都是透過種植能源作物來著手,如巴西的甘蔗、美國的玉米和大豆等,藉由將這些作物轉換為一般可以利用的能源形式,多半是燃料,來替代使用化石能源。
不過於我國而言,不可能如這些國家透過大規模的種植來降低生產成本[2],反而會因為種植能源作物來排擠一般糧食作物的生產,如美國就是因為種植能源作物降低生產糧食的比例,固然使得美國農民的收入提高,但是卻造成其他國家的糧食價值大幅提高,如果從整體來說,我們可以說美國農民額外的收入是來自於那些國家額外支出購買糧食的費用。而我國也的確有可能因為降低糧食生產的結果,造成糧食自給率的降低,固然我們可以從能源作物的生產獲利,但是考慮糧食進口的可能的額外支出後,未必對於國家本身有利。
此外誠如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所言,如果將生產能源作物本身所投入的能源一併考慮進去,有可能儘管能源作物可以作為能源來源,但是其投入之能源反而有可能會高於能源產出,或是將能源作物透過轉換後可利用的能源,甚至不比將能源作物本身作為燃料的更多,這一點也在在駁斥我國支持生產生質能源作物的論調。
但是在生物科學和農業科學研究者眼中,這當然是低估了我國可以利用的資源和生物科技本身發展的潛力,特別是如果認為可以透過能源政策促進能源科技的發展,那麼當然也可以適用在生物科技的發展上。
農業廢棄物的再利用
不過對於我國來說的確也有著可以降低生產生質能源的作法,不是透過生質能源作物,而是經由一直以來農業上被忽視的農業廢棄物這一塊。
農業廢棄物在我國最大宗就是生產糧食作物中所產生無經濟價值者,最常見的是稻桿、研磨糙米的米殼等[3],但是以往的處理方式為就地焚燒,然後將灰分作為鉀肥,但是在燃燒過程中所產生的熱能就會全部散失掉,而如果可以將這些農業廢棄物用作生產生質能源的原料,我國則並非沒有可以和外國競爭的能力可言。
加上將農業廢棄物作為生產生質能源的原料,不只可以增加能源來源,另外可以降低處理這些廢棄物時所造成的環境汙染和處理成本,而一直以來政府對於稻桿等廢棄物的處理方式都是容許就地焚燒,
基改作物在生質能源上有相當發展的空間
的確如蕭代基院長批評我國在發展生質能源作物上無法及於巴西或是美國的先天條件,但是那是在於使用同一種作物的假設下,同樣為甘蔗而言,我國集約農業所投入的人力、肥料成本都會比起巴西和美國粗放式來得高,可是如果可以將這個壓力作為助力,促使我國在這方面進行改良品種的研究,當然也有可能在我國狹小的耕地上發展出超越他們的成果。
在品種改良上,就是透過基因轉殖的方式創造出新品種作物,有著高於傳統作物的產量、耐旱、抗寒、抗病蟲害等優點,不過在作為糧食作物上來說,考慮到對於環境的副作用,人民和政策在數十年來對於基改作物都是持保守態度[4],因此在欠缺市場的情況下,在我國自然基因轉殖的技術無法利用在生產作物新品種上,只能使用傳統緩慢的研發育種方式。但是如果作為研發能源作物的方法,當然就是一大利器。
政策配套
當然方案本身也需要有政策的配合,於這一點無論是將農業廢棄物作為生質能源的生產原料或是透過基改作物為之,都會面對到直接讓其進行市場競爭或是透過經費補貼的方式加以扶植,在這方面來說,的確以經費補貼會造成較無效率的結果,因此在學者的意見中[5]認為最上策是透過能源稅的課徵來造就人民進行替代化石能源的研發,然後完全交由市場競爭的方式,中策才是在於透過補貼淨能源產出高的政策補貼工具。
在農業廢棄物處理上來說,確實可以透過上策來促使有企業願意從事這一塊產業,畢竟比起種植能源作物來說,直接以低價取得農業廢棄物更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但是在基改能源作物上則更需要政策的配合,這方面則需要透過專利法和植物種苗法先對於基改作物研發成果的保障,作為研發生產的誘因,再來是在農委會政策上放鬆對於基改作物的限制,否則即便研發生產,也沒有可能透過市場競爭找出最有利於能源政策的基改能源作物。
結語
在能源危機成為全球各國密切思考的問題的當下,我國除無法自身於國際潮流外,更還有先天上能源自給率低的不利因素,因此仔細考量以上各界學者對於政府能源政策的建議,找出我國在面臨危機時的出路,是政府勢在必行的當務之急。
[1] The Economist, 2006. Pocket World in Figures.
[2] 以生質酒精的生產為例,採粗放農業的巴西生產成本為每公升6元,美國為10元,但是同為集約生產方式的中國大陸則為16~20元,而我國的生產方式和中國大陸雷同,只是土地規模更小,更不可能大規模生產,想來成本更在這之上。參照 農委會農業試驗所林俊義所長,《打造綠色油田-生質能源之開發》2007.11.24
[3] 在農委會所列之農業事業廢棄物中很少包括作物廢棄物,而多是在規範家禽家畜生產過程的廢棄物需要透過如何規格化的處理方式以防造成汙染,而農產品的廢棄物則是認為透過焚燒或是碾碎當肥料為之,難以進行有經濟價值的再生產。參照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
[4] 當然這與其說是基改作物對於環境或是生物體本身可能造成副作用,更大的理由是在於我國一直沒有如其他國家一樣迫切感受到糧食價格高漲的影響,像是墨西哥等國就因為糧荒而產生暴動。因此對於糧食政策就沒有如同能源政策來得積極,也一直不熱衷於推動糧食作物的研究,而只是一味使用傳統需要耗費數年或甚至十數年以上的育種技巧,而不願意投入基因轉殖技術於糧食作物中。參照 中研院分生所 余淑美研究員,《植物分子農場生產生物製劑》,植物種苗生技第九期,頁38-41,2007年。
[5] 參照 蕭代基《最佳的、次佳的與不佳的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經濟前瞻第35期,頁35-37,2007年。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週四, 13 六月 2024 22:03
學生短評精選-涂若筠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全球環境政策與法律專題討論
1012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演講心得
經濟取向的能源政策?
國際法組二 涂若筠 R97A21112
一、前言
在工業革命之後,地球資源被大量開採,許多國家成為經濟大國,當人們意識到資源的有限性時,便上演資源爭奪戰,引起國際情勢的緊張甚至戰爭,即使曾經經歷石油危機,人類依舊不斷開發地球資源,並對環境生態造成嚴重破壞,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災變導致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與此同時,人類也逐步邁向能源耗竭的危機。
為了解決能源與環境問題,各國召開多次高峰會,並簽訂相關議定書、條約,不同國家亦提出不同的能源政策,對於台灣的能源政策,蕭代基院長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對於蕭院長的見解,我有贊同與不贊同之處,以下將分別以再生能源之發展與綠色稅制之採行兩部分進行說明。
二、再生能源之發展
生質燃料是再生能源的開發項目之一,當美國大量種植玉米以轉換成酒精時,卻排擠其他糧食作物之耕種面積,導致價格的提升與其他國家的糧食危機,然而,玉米酒精並未帶來應有的效益,其他生質燃料,例如大豆製柴油,甚至排放出更多的溫室氣體,且在製造生質燃料的過程中,也耗費相當多的能源與人力,亦可能造成溫室氣體的排放,依照蕭院長的觀點,在投入生質燃料的開發前,應仔細評估成本效益,才能為之。
生質燃料的開發與否,除了經濟成本與環境保護效果的考量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應為糧食危機,從美國大量種植玉米導致小麥價格高漲,並引發以玉米為主食的墨西哥必須以汽車爭奪糧食的緊張局勢,可看出一味發展生質燃料可能帶來的危機,此已可能涉及人權問題,把空間拉回台灣,台灣土地狹小,可耕種面積未如其他國家廣大,倘若一窩蜂種植能源作物,將會排擠已為數不多的稻米耕作,當一國之主要糧食無法自給自足而需要完全仰賴進口時,假若遭到封鎖,則將陷入嚴重危機,因此,維持一定的糧食耕作是必要的,政府在推動開發生質燃料前,亦必須考量攸關人權的糧食問題。
除了生質燃料外,太陽能、風力、水力亦屬於再生能源,蕭院長認為政府所應補貼者係為再生能源科技之研發,而非價格補貼,此頗値贊同,因價格補貼無法使市場進行淘汰機制,再生能源科技之研發則可以保存真正具有效益的科技。
雖然蕭院長強調節能之重要性,對於再生能源之發展似乎有所保留,但面對能源逐步耗盡,開源亦相當重要,對於環境負擔最小的開源更為重要,當科技發展使人類可以充分利用太陽能、風力、水力的再生能源時,將會減少地球環境的負荷,如同電影「搶救地球」所述:「哪一個地方沒有陽光?哪一個地方沒有風力?」位處亞熱帶的台灣,具有充足的陽光,澎湖、恆春等地具有強勁的風力,在高山陡峭之處,亦有發展水力之潛能,當台灣在進行開源時,應考量所擁有的自然資源,並將這些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為最大的利用,政府並應針對這些科技之研發給予相當的補貼。
三、綠色稅制之採行
蕭代基院長認為國家應該課徵能源稅與環境稅,其理論源自於使用者成本、污染者付費原則、雙重紅利(四重紅利)與能源安全,這些新增稅收的所得則可用於低收入戶所得補貼、補貼大眾運輸、取消四種貨物稅、印花稅及娛樂稅、調降所得稅及營業所得稅、改善財政收支並用於研究發展,並根據Weitzman理論,短期以碳稅之課徵為減量工具,長期以總量管制,即碳排放交易為減量工具。
為達到降低碳排放量,綠色稅制與碳排放交易之採行似乎是勢在必行,根據蕭院長的說法,此項政策對於長期經濟是有所助益的,假使高耗能產業無法在此政策下存活,那就只能讓他們出走或倒閉,此為經濟發展所必須之陣痛期。
對此,我卻有所質疑,根據目前的調查,台灣碳排放量之大宗為台塑集團與台灣中油之企業,一個是台灣數一數二的大集團,一個是國營企業,這兩大企業可推估其能夠負擔綠色稅之課徵,然而其他較小的企業呢?當這兩大企業繳稅後繼續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其他較小企業因無法負荷而出走或倒閉,減少的只是少部分的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卻是上萬個失業人口與其背後的家庭負擔,就如同加入WTO後,農業與其他傳統產業所受到的嚴重衝擊,但政府並未以其他配套措施加以有效輔導,受到最大衝擊的是這些原本就收入不豐的人民,也因此可以看到許多國家的農民與受衝擊之勞工對於WTO與其政府之大規模抗議活動,當政府努力與國際接軌推行綠色稅制之時,是否又對中小型企業造成另一波打擊?政府若沒有足夠的配套措施,所侵害的是這些人的工作權與生存權,這難道是為了未來經濟前景所能夠犧牲的?這場遊戲似乎也只有資本主義與大財團才玩的起。
這些綠色稅之課徵者如為中央政府,稅入又該如何分配給地方政府?是否應該由受到較多污染的縣市獲得較高的分配?若課徵者為公司營業登記地,所多大企業之登記地為台北市,但很明顯的,其工廠與污染之排放地為高雄地區與雲林地區,這豈不成了「稅留台北,污染留給高雄與雲林」的荒謬窘境?
除了國內本身的失業問題外,當這些產業無法在國內生存而出走到其他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時,亦將對該等國家造成污染,而溫室氣體之排放也不過是從台灣改到其他國家而已,全球總體排放量並未因此減少,溫室氣體之排放系具有全球性的,當許多已開發國家紛紛採行綠色稅制與碳排放交易時,企業便紛紛前往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減少的只是某單一國家的排放量,溫室氣體之總體排放量依舊未減少,難道這就真是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嗎?或者又只是駝鳥心態的眼不見為淨?真正受害的卻是那些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之人民,且當氣候變遷造成極端災變時,這些國家又會受到嚴重的衝擊,其所需要的復原時間又比已開發國家長久,這又成了已開發國家對於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之侵害,一種資本主義大國之遊戲,假如此種政策只注重單一國家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而未重視溫室氣體的全球排放量,那似乎是過於狹隘了。
四、結論
每一項政策之制定,必須考慮許多面向,不應以單一面向決定政策之全部,政府應該有全面性之考量,這才是負責任之政策。
能源政策之推行對於現今與未來之環境保護具有相當大的重要性,但在制定能源政策時,似乎不應該只重視經濟取向,政府應該重視被犧牲者之人權,採取配套措施或相關的社會福利政策,亦應評估對於其他國家之影響,從全球宏觀的角度來思考,因此,能源政策之制定,除了經濟取向外,還必須加入人權取向、社會福利取向以及國際環境取向。
一項政策之推行會造成數十年之影響,可以想見不良的政策會帶來多麼可怕的後果,受害最深的往往是無法參與決策之人民與後代子孫,國家在制定並推行政策時,應該經過深思熟慮與通盤考量,期望台灣能夠有更完善、細膩的的能源政策。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週四, 13 六月 2024 22:01
學生短評精選-辛年豐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碳排放管制手段的政策分析
辛年豐*
人類社會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發展之後,對環境造成高度的破壞,也產生許多的污染,經過日積月累的結果,使得當前我們所面對的污染問題更為嚴峻,除了對環境的直接破壞及污染之外,也因開發過程的過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嚴重的溫室效應,並對全球氣候造成影響,也釀成不小的災害。為了因應這樣的問題,許多國家簽署了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並本此公約訂定了京都議定書,確定了在全球的層次下,以「排放權交易制度」做為碳排放的管制工具。然而,這樣的管制手段是否適合目前的臺灣加以運用?乃至於臺灣為因應國際的趨勢,也有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的立法芻議,但這樣的立法與其他既有的環境法規之間的關係,如從法政策面加以考量,其適當性也有進一步考量的空間。
碳排放的多種管制工具
在現有的環境行政管制當中,有許多的管制手段,其中採用經濟誘因的管制手段,除了有課徵能源稅及環境公課兩者之外[1],還有採用總量管制的方法,及補助及預先支付回收金的制度[2]。由於能源稅及環境公課都是國家向人民收取一定額度的金錢,具有相似性;而總量管制則為人民之間就國家所定排放量依市場機制進行交易,而使該排放量在市場上做最有效率的發揮,與國家向人民收取稅賦相較,是為追求同一目的,完全不同的做法,而可進一步比較兩種制度的良莠。因此,本文在此僅針對能源稅、環境公課及總量管制這三種管制手段加以討論。
所謂「能源稅」,是透過課徵一定稅收以反應邊際使用者成本,其所反應的代際間的外部性及人類使用能源對環境所造成的損害,主要的目的並非在反應環境外部成本;反之,環境公課則在反應環境外部成本,因環境外部成本與污染物排放量有直接關係,而與能源使用量的關係較弱,因此,以污染物排放量為稅基的環境公課來反應環境的外部成本[3]。而「總量管制」,則指在一定排放量對環境有助益的限度內,由國家設定最高的排放量,而使該排放量具有一定的市場價格,讓各個主體就這些排放量進行交易[4]。在現有的空氣污染防治法中,也都採用這些管制工具;而在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的設計當中,則延襲京都議定書的機制,採總量管制的手段做為管制工具。然而,在現有的這些排碳量的管制工具中,在法政策上,究竟要如何安排,較符合我國需求,也有待進一步討論。
管制工具的選擇
就以上採用能源稅、環境公課及總量管制的手段來達成減少排碳量的目標,在法政策上,究竟要如何安排較符合臺灣需求?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蕭代基教授主張基於「避免兩者同時執行將產生競爭效果」、「課徵碳稅對象較為全面」、「碳稅所可含蓋的範圍較廣」、「以稅為管制工具適合短期管制,以總量管制為管制工具適合長期管制」、「碳稅所蒐集的資料有助於將來排放量交易資料庫的建立,簡少交易成本」等理由,認為因碳稅交易成本低,排放交易的交易成本高,故臺灣應採取「碳稅先行,排放交易後行」的策略。如此的策略思考,固然與臺灣特有的國際地位有所關聯,而認為我國短期之內不一定會受到國際公約的直接拘束;然而,本文以為這樣的策略似有再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固然,本文不否認兩種管制工具同時進行會有競爭效果,但為何基於這樣的理就要犧牲掉排放交易的管制工具,是有待從其他理由的檢討得到進一步答案的。首先,本文當然不會否認課徵碳稅的課稅主體較為全面,所可含蓋範圍也較廣,但這也是採用「稅」做為管制手段本質上的必然,當採用「總量管制」做為管制工具時,本來就會有範圍較窄、對象較少的問題。詳言之,這兩種管制工具本來就是針對不同的對象與範圍,當有總量管制的制度時,需要排碳的事業體,就必須有一定的排碳量才能維繫其事業的生存,不會因此就使碳稅的課稅主體縮小,也不會因此縮減課徵碳稅的範圍。簡言之,採用總量管制並不會影響到課徵碳稅的範圍與課稅主體,故以此理由說明現階段臺灣不適合行排放權交易制度,並不見得妥當。又即便這樣的理由有道理,但這本身存在著一個內部的矛盾關係,亦即,同屬碳稅範疇的能源稅及環境公課,也同樣有課徵範圍大小的問題,通常,後者僅限於固定的事業體才有可能需要繳交環境公課,以回饋該事業體對於環境的傷害。因此,環境公課的對象及範圍當然遠比能源稅為小,如以課稅主體小及範圍窄做為「後行」的理由,是否也因此要認為環境公課的課徵要先暫緩。但實際的情形是,在我國目前的環境法規中,環境公課的制度業已於空污及水污等領域施行,但並沒有產生什麼問題。
同樣的,以管制工具適合長期管制或短期管制也有類似的問題,因臺灣社會的運作本來就是要追求長期永續的發展,這兩個管制工具並沒有階段的問題,採用長期的管制手段並不會妨礙短期管制手段的施行。因此,以此做為目前不進行總量管制手段的理由並不充分。再者,碳稅所建制的資料有助於降低交易制度的建制,這也是可以從制度面解決的,因目前的空污法及水污法,就排放權制度的運作也具有一定的基礎,相關排放權交易制度的建置,應不至於因沒有經驗而無法運作。又即使有這樣的問題,也可以在行政組織做適當的設計,讓碳稅課徵與排放權交易隸屬於同一行政機關或單位,使兩制度的運作有相同的資料庫可以互通。如此一來,更可降低機制建立的成本,同時,也可讓這兩個制度同時運作。
而採用總量管制的手段,除了是京都議定書所採用的手段之外,在國際上諸多國家多已奉此機制進行行政管制,如日本於1998年制定了地球暖化對策促進法,並於2002年及2005年因應京都機制做了修正,都為了可以做排放權交易而準備[5]。如此的世界潮流鄭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國如也能運作同樣的制度,在將來勢必較能與全球環境管制的潮流接軌。否則,一旦我們的制度較為落後,將來施行時也將必須付出更多的學習成本,同時,在國際交易市場及國際貿易上,也可能因此處於弱勢的地位,所要付出的代價恐怕將會更高。在制度上,本來碳稅及總量管制就具有不同的功能,兩者並不具有當然的互斥關係[6]。因此,為了可以達成各自的制度目的,本文以為在政策考量上,當以碳稅與總量管制兩者併行為妥。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博士班公法組學生,學號:496668022。
[1] 松村弓彥,《環境法》,成文堂,2004年4月10日二版,頁77~78。能源稅在日文文獻中,稱為「環境稅」,而我國所稱的特別公課,在日文則稱之為「課徵金」。而在我國,對於環境公課亦有稱之為「環境稅」。
[2] 大塚直,《環境法》,有斐閣,2006年4月20日二版,頁83~84。
[3] 詳見蕭代基、王京明、黃耀輝,<能源稅是永續發展稅制改革的契機>,經濟前瞻,2007年7月5日,頁107~108。
[4] See James Salzman, Barton H. Thompson, JR,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Thomson West, 48~49. (2nd 2007)
[5] 大塚直,前揭書,頁141~142。
[6] 但韓國於空污的管制上,在採用總量管制的事業體,可免除排放主體繳交特別公課的義務。詳見朴勝俊,<日本と韓国の大気汚染総量管理制度と関連賦課金─韓国の首都圈大気環境改善特別法における排出枠取引に注目して>,産大法学第41卷,第3号,2007年12月,頁22。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週四, 13 六月 2024 22:01
學生短評精選-李崇菱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Energy Security and Related Climate Change Issues: Taiwan Perspective
Seminar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Semester 98-1
Class Reflection Paper
李崇菱 Tsung Ling Lee[1]
R95A41013
I. Introduction
As the earth heats up during the recent year, so does the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the urgent need to readdress the global problem as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in recent years. This is more so in 2009 as Taiwan experienced the devastation after typhoon Motakot swamped the southern Taiwan in August; and in the subsequent month, Typhoons Ketsana and Parma hit Philippine coasts; the weather anomalies and human devastation demands global attention and the execution of a workable global solution.
In light of this, Taiwan serves as an interesting microcosm for climate change, because as a tropical island nation it is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to rising seas and temperature. For example, as a comparison the temperature in Taiwan has risen 1.43°C since last century, which is twice the world average of 0.6°C. If sea level rises by 1 meter, Taiwan risks at losing 274 square meters of land. Moreover, Taiwan has a heavily industrialized economy, where currently it ranks 26th as the world largest economy and produces around 1% of the world total greenhouse gases (GHGs). During the past 18 years, Taiwan’s carbon dioxide (CO2) emission has grown by more than 140%[2], continuing with business as usually, would almost certainly means a dangerous and a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 is highly probable, this is a route Taiwan can ill afford.
II. Taiwan and its Energy Security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poll conducted by Taiwan Public Opinion Studies Association released in June this year, the awareness on climate change has increased in the recent years, as nearly twice as many Taiwanese people believ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economic development[3]. However, the top three environmental issues ranked by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oll are landscape preservatio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While it is encouraging that the public has become aware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likely impacts, however the ranking of environmental priority reveals some worrying concerns, as it indicate that people are underestimating the gravity of the problem. This is disconcerting, particularly in Taiwan context.
As a matter of fact, in terms of energy supplies, Taiwan relies heavily on foreign suppliers where 42.3% of its coals supply comes from Australia, 36.9% are imported from Indonesia, and China supplies approximately 16.8 % of coals to Taiwan[4]. These imported coals are used for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steel, cement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5]. Domestic coal production stopped in 2000, and the coal shortage is mostly met with imports. Moreover, in terms of oil consumption, where it occupies the largest share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 Taiwan (45.7%?),[6] Taiwan relies on Saudi Arabia, Kuwait, Iraq and other middle east countries for its oil supplies. Both coals and oil supplies in Taiwan comes from imports, the inadequacy of domestic energy production poses hidden danger to Taiwan,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security of oil supplies is subject to volatil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urbulent regional geo-politics which Taiwan has little influence. To prevent supply disruptions, refiners in Taiwan are unde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to stock no less than 30 days of consumption, an energy policy similar to those of Japan and South Korea[7].The majority of the oil consumed in Taiwan is by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ough refiners in Taiwan are under regulatory requirement to maintain base level of oil supply, the absence of alternativ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supply, poses hidden danger to Taiwan industries and exposes the vulnerability of Taiwan in the international realm which must not be overlooked.
III. Law and Policy: two sides of a coin
How policy is implemented and executed is dependent on the perimeter set out by law, and law gives weight and actualizes the grand venture envisaged by policy makers. This is particular so in light of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energy policy, where a cohesive energy policy is desirable, and the law regulates and sets to achieve the desirable outcome of public policy, where, in theory should based on the interest of the public, and the nation as a whole. However, given the trans-boundary nature of climate change, where polluters might not be subject to “gree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for those advocators of green energy might still suffer the consequence of climate change, it highlights the political sensitivity and the grand-scal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This is global challenge that demands global effort and global strategy;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with effective means and to slow down global warming, would inevitable invite a paradigm shift that departs from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state-centric thinking; where nation-state implement their own “command and control” approach. This become prominent when the scope of harm does not know borders, policy decision needs to be made at a supranational level for it to be effective, yet at the same time regulatory authority at international level risks centralizing decision power and isolate nation-states from the decision process, thus rending the process at risk of democracy deficit.
However, without a coherent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system and functional governing body, all efforts and good wills of individual nations might go astray in mist of a battle to combat global warming. This is because climate change is not a confined local or a regional problem; the temperatures are rising, the sea level is ris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real and are happening at a much rapid pace than predicted[8].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is the rise of preval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typhoons, environmental refugee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polluters in responsible and contributors of global warming. In mist of climate chaos, humanity as a whole for the first time, have to face the price for industrialization, regardless race, age, nationality, religion, and sex. The commonality of the problem demands the readdress of the issue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Hence, when dealing with law and policy of climate change, I propose the following. Climate change is a multifaceted issue, and it should be dealt with as such. For example, to combat and halt global warming through the control of GHG emission, a unilateral state action is neither inadequate nor feasible because it does little when the big picture is considered. Take the Kyoto Protocol for example, despite some attempts to decrease carbon emission of its committed signatories, whe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produces the largest amount of GHG emission refused to ratify the treaty, the Kyoto Protocol achieves little and expires soon in 2012,[9] and post-Kyoto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is underway. To monitor and to decrease global GHG emission, state cooperation is vital and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monitoring agency is critical to success. Nevertheless, for climate change agenda to gain its full momentum and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for states, consensus from state actors must take the form first. However, how to achieve the agreed target or how to implement the relevant operational mechanisms, there should be flexibility for state actors to decide. States actors must allow the freedom to implement and choose the suitable instrument, which reflect its domestic needs and balance its self-interest, and this will increase the incentive for state actors to commit to the cause.
IV. Carbon Tax vs. Cap and Trade
In other words, so long as state actors all acknowledge that climate change is a top priority in its national agenda, then how to implement the relevant acts should be subject to state actors’ discretions. For example, the debate over carbon tax and cap and trade system is much heated debated on the climate change scene. Both sides of the camps present creditable arguments; where cap and trade imposes an overall cap on permissible emission level in th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benefit it provides certainty that results from its implementation (benefit certainty), and because cap and trade operates on market-basis, the cost is uncertain. Whereas carbon tax sets the precise amount of tax in advance, it provides cost certainty, but it does little to warren the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 and does not offer benefit certainty[10]. Hence, on the international realm, which route to take in an effort to combat global warming should be subject to state actors’ discretion, where government chooses the instrument that is most suitable for its domestic economy and structure, and might less the concern of democratic deficit. However, an institutional monitoring mechanism must be in place, where bad behaviors are punished, and to monitor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process,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i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allowing two competition economy models to co-exist, carbon tax and cap and trade, in reality would complicate the daily running of business, but since no one is certain which one is more beneficial while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is real, two competing economy model might counterbalance and counteract each other’s deficiency. At supranational level, the institutional focus should be on how to monitor the competing economy models and to coordinate the inherent devia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ensuring all available data gathered such as external costs, efficiency, etc. are accessible to all.
Interestingly, in relation to Taiwan’s scenario, Dr. Daigee Shaw[11] from Chung-Huan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CIER) purposed Taiwan should implement carbon tax for a 10-year period, then follow by the adoption of cap-and-trade system. The underlying argument is to avoid the complications between the executing of dual competing economy models, which is the current state in the European Union where emission trade scheme (ETS) and carbon tax run concurrently[12]. While simplicity might be the preferable route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by taking the carbon tax route for a 10-year period, Taiwan might risks being marginalized from the cap-and-trade system when it would be a well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economy norms in a decade.
V. Private Innovations and Regenerate Energy
While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 is dependent on political negotiations and complicate political reality that often result in political comprise, at domestic level, government should commit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as the centerpiec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structure[13]. While Taiwan is not a party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14], Taiwan voluntarily abides to the UNFCCC objective[15]to reduce its GHG emission. Revit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ime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and induce creative thinking, inventing, funding, testing, refining, and commercializing new technologies[16]. This is where the private industry consistently outperforms the public sector;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coil from “command and control” approach and establish a regulatory framework that monitors private sectors’ environmental progress while establish incentives for private sectors to invest in green technologies by rewarding innovation. By shifting innovative process to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will not only increase the scale and diversity of innovation, it is also likely to increase Taiwan’s international profile, as well as enhance Taiwan’s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While the initial investment in green technology is costly and often acts as a financial obstacle for private sectors, the role for government to play is to set the environment standards and structure incentives that encourage business and industry to invest through laws and regulations.
Despite the promising results of biomass energy, in reality,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biomass energy, the amount of carbon dioxide must also be accounted.[17] Though production efficiency is one plausible consideration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holistic approach is preferable as it considers other factors such as agricultural profitability,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market etc. In other words,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regenerated energy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o discard the potential of regenerate energy as alternative fuel because its inefficient production method, would ignore the potential and a probable more sustainable solution. As with any source of energy, regenerate energy needs time and technology to mature for it to be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To deny regenerate energy the chance of further technology investment because of its production efficiency at its infancy, is to deny a probable solu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VI. Conclusion
In short, the effects and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inevitable and would worsen if no collective global effort and collaboration are taken. Taiwan as an island nation serves as an interesting microcosm for climate change, and how Taiwan implements its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can reflect and mirror the efforts to halt global warming at international level. However, since climate change is a transboundary challenge with multifaceted dimensions for the new century, to tackle the global problem must resort to collective strategy and coordination, otherwise any attempts by individual state actors would be futile and nugatory.
[1]By submitting this paper, I thereby waiver copyright should the paper be accepted to publication subject to revision.
[2] EETO head warns on climate change, Taipei Times, June 18, 2009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09/06/18/2003446466
[3] Ibid
[4] See class presentation PPT “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presented by 林季陽,林薇真,林恆翠
[5] Ibid
[6]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Energy Statistics from the U.S. Government, http://www.eia.doe.gov/listserv_signup.html
[7]Ibid
[8]David Shukman, Four degrees of warming 'likely',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8279654.stm
[9]Emissions Trading Directive 2009, http://en.cop15.dk/blogs/view+blog?blogid=2063. Also se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Kyoto Protocol, Dec. 10, 1998, 37 I.L.M. 22 [hereafter Kyoto Protocol].
[10]Reuven S. Avi-Yonah, David M. Uhlmann, Combat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Why A Carbon Tax Is A Better Response To Global Warming Than Cap And Trade, 8 Stan. Envtl. L.J. 3(2009), See Also Brian C. Murray & Heather Hosterman, Climate Change, Cap-And-Trade And The Outlook For U.S. Policy, 34 N.C. J. Int'l L. & Com. Reg. 699 (2009)
[11]http://www.cier.edu.tw/ct.asp?xItem=9758&CtNode=234&mp=2
[12]Sweden, Denmark, Finland and Slovenia have taxes on household carbon emissions resulting from heating and electricity use.
[13] Daniel C. Esty, Breaking The Environmental Law Logjam: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17 N.Y.U. Envtl. L.J. 836 (2009)
[14]Taiwan needs to participate in UNFCCC, ICAO: Premier Wu http://www.carbonoffsetsdaily.com/news-channels/asia/taiwan-needs-to-participate-in-unfccc-icao-premier-wu-16476.htm
[1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Yuan, R.O.C (Taiwan) http://www.epa.gov.tw/en/
[16] For example, The Act Governing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lays down a legal framework to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and offer incentives to local consumers to install renewable energy equipment. See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biz/archives/2009/10/03/2003455073
[17]Dr. Daigee Shaw, Class talk, Monday, 12th October, 2009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週四, 13 六月 2024 21:59
學生短評精選-林季陽
*本文為回應10/12中華經濟研究院蕭代基院長<氣候變遷與能源政策>專題演講,學生短評文章之精選。已獲作者之授權,刊登於本中心網站。
不同經濟思維下的能源政策—對能源稅與生質能源政策的再思考
科法四
R94A41016
林季陽
蕭院長演講重點主要討論下列四點:生質能源、綠色稅制、碳交易以及結合綠色稅制與碳交易之設計。本文選擇聚焦於討論以不同經濟思維來就有關生質能源政策與能源稅重新思考現行政策。故文中將翦除部份略為瑣碎之心得論述。
蕭院長於討論生質能相關政策時,其選擇標準(criterion)似以淨能源分析與成本效益分析為出發點。例如淨能源產出數值(EROI)、NPV等方式[1]。此類選擇標準其出發點均源自經濟學上所稱之效率,然而此處效率如何定義,仍有討論空間。蓋一般經濟學上之效率,為求衡量之便,多以經濟利潤、貨幣價值為代表之,然便如張老師所提出之疑問所示,成本效益分析如何呈現質化面向,即效率之外的環境政策所追求之其他價值,仍是量化研究所無法克服之先天缺陷。且該成本效益分析,亦無法呈現各項再生能源科技在技術發展上是否有所突破此一重要因素。此外,近年來開始發展的綠色經濟思維即非單純以貨幣價值來衡量經濟效率[2]。是以,蕭院長所提之淨能源產出與成本效益分析部份,其所得數值自應慮及上開限制而對基於該數值所做出結論採審慎之態度。
另一方面,若立基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緩和氣候變遷之影響,生質能源之選擇準則上,實應將是否達成碳中立為優先。成本效益分析應退居較後順位的選擇準則。蕭院長認為不應由政府來選擇替代之生質能源,若以經濟自由主義觀點出發,自然採此立場並不意外。然而學生本於經濟領域背景,實應說明蕭院長此看法僅係經濟學上見解之一支。縱以蕭院長於演講中所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Stiglitz來說,實際上在其名著『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中便對基於貿易理論所發展出的全球化政策有所質疑[3],認為基於純理論所建構出的政策建議若未考量各國之民情、歷史脈絡而逕行實施,未必能達成理論所提示之經濟效益,且在歷史經驗上也證實此一說法。因而在此應說明,並非所有研習經濟學之人皆服膺應交由市場來決定此一見解。畢竟就經濟史角度觀之,亦不乏經市場競爭後所達成結果,事實上未較有效率之例證。
另外,關於蕭院長所提出之綠色稅制,其理論基礎在於綠色稅制應反映使用者成本與代際公平,依其公式,自然資源價格=邊際機會成本=邊際生產成本+邊際使用者成本(能源稅)+邊際環境外部成本(環境稅,EX:空污費)。然而若同時考慮污染者付費原則,為何支付環境稅者不應同時支付能源稅,似有疑問。再者,蕭院長對雙重紅利甚至三、四重紅利所抱持的信心,似乎在理論與實證基礎上仍顯薄弱。除未就國內外對雙重紅利效果持質疑態度之文獻予以回應外,亦未就歐盟等已採行能源稅、排放權交易等國家,其施行至今所面對的問題正面回答。此部份具體內容,將在下段呈現。
首先,短期碳稅較佳,長期排放交易制度較佳的講法,係哈佛大學教授Weitzman在1971年所提出之定理。雖謂定理,但首先不可忽略其係建立在眾多非真實之假設上的推論。是以對其結論之應用,自應審慎為之。再者,蕭院長就學生對稅率訂立之提問的回答,實難認非有前後矛盾之情。蓋若認稅率由bargain行為所產生,首先無異於要求對課能源稅採反對態度之利益團體,對增稅此一劣等財去喊價,實難想像如何有此經濟誘因。第二,蕭院長所奉之的歐美能源稅,其稅率亦非由bargain產生,而係基於複雜之經濟方法所試算得出。因此恕學生難以苟同蕭院長直接否認一般均衡模型(CGE model)可以求算出稅率之論點,蓋其理由僅以要考慮太多因素,然而這似又與bargain只考慮利益團體本身經濟利潤來決定稅率之論點產生矛盾。
必須強調學生的立場並非單純否認碳稅或能源稅不具有政策工具之價值,而僅是對說理有所不足的政策建議持保留態度。蕭院長甚至舉歐盟之能源稅價格為20歐元為例認為,然而為何我國必須曹規蕭隨?各國有自己不同之產業結構,總體經濟環境、物價水準,況歐美之能源稅尚區分從量稅、從價稅,蕭院長在說理上亦未予區分,此似因時間因素所致,實為可惜。
最後蕭院長對於增稅造成產業出走之提問的回答,實可謂是一般經濟學者與非此背景出身者於溝通上最大的鴻溝。經濟學在邊際革命後,披上科學之外衣,認為經濟判斷應獨立於道德判斷。然而政策判斷如何能自外於道德判斷?況且縱依純粹經濟判斷,產業出走後並非直接連結到產業轉型,尚應考慮此舉牽涉到其所造成的社會成本等外部成本,此即與本文前述經濟效率之定義有所關連。但若僅以此為轉型陣痛而應由人民自己概括承受,做為政策建議者,學生認為似乎是一不負責任之行為。對此,本文建議『全球化之許諾與失落』一書便值得一讀,其內容便指出世界銀行與WTO組織依自由貿易理論採行的政策建議,在世界各地所施行後所帶來的好處與所製造的災難。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週四, 13 六月 2024 21:57
2009年10月5日課程內容:氣候變遷、能源管制與能源安全- 台灣觀點與國際視野

壹、前言:氣候變遷與能源問題所延伸出的環境法律政策思考
氣候變遷所帶出來的相關議題當中,能源管制及能源安全可以說是最首要的問題,牽涉也相當複雜。不過,問題儘管複雜,但其解決方法的思考,卻也都不脫環境法律與政策思考的基本方向。環境法律與政策的研究方法,首重背景事實的掌握,在正確瞭解事實之後,才能進一步發現並整理問題之所在,再以此出發來思考法律與政策所能扮演的角色。
以台灣的能源問題為例,我們首先必須瞭解台灣目前的能源來源與能源結構,才能思考能源價格與能源安全的問題何者須優先處理,何種政策在現今情勢下有必要先行。而法律與政策間的關係,有時法律隨政策而生,有時政策後於法律出現,兩者也可能互相交錯影響;在能源政策的問題上,不僅事實面的問題必須掌握清楚,法律與政策的對應關係,也必須列入考慮。
貳、臺灣的能源問題
從許多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臺灣的能源結構問題在於我國極少自產能源,依賴外國能源輸入高達總能源使用的97.9%,且石化能源使用之比重相當高。試想如果運油船被中國封鎖,臺灣所貯藏的能源能維持國家運作多久?這不但涉及能源正義,更是能源安全的問題。
除了前述自產能源低所導致的能源運輸安全問題外,台灣能源使用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與GDP成長的分離(de-couple)也遲未出現。相較台灣,OECD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GDP成長於1990年開始分離;亦即,GDP繼續成長的同時,能源使用及溫室氣體的排放卻逐漸減緩。這也是京都議定書以1990年為溫室氣體減量基準的原因。臺灣至今尚未出現經濟成長與污染排放量分離的現象,甚至能源使用量還一路上衝,這代表我國的能源發展形態有根本性的問題。已開發國家已經在轉型,但臺灣卻改變的十分緩慢。
接踵而來的問題是,即使產業配合轉型,如果不清楚工業部門當中佔最大宗排放溫室氣體的業別是哪些,例如少數業別可能佔GDP極低,但卻有極高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則轉型未必有實益。即使成功轉型,固然排除了某些既有的污染產業,但也不意味著新興產業就一定是低溫室氣體排放、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產業,如果新興產業沒有對其能源效率或溫室氣體排放量進行一定的環境影響評估,則所謂新興產業也不見得就一定比傳統產業更節能,對環境更有益。這些問題,都是台灣必須予以嚴肅面對的能源課題。

參、能源法律與能源政策之爭議

參、能源法律與能源政策之爭議
能源法律與能源政策必須相互配合,才能發揮最大效益,但有時兩者卻有先後、甚至是矛盾或衝突,「綠建築」相關的政策與法律就是這樣典型的案例。近來台灣社會已經逐漸有「綠建築」的觀念,也逐步落實在實際的建案中,例如我們法律學院在校總區的這兩棟新館。不過,國內公私部門的建材尚未規格化,既有管制規範也十分寬鬆,均不利「綠建築」的發展。民間即使主動願意作,也會面臨既有法律的限制,更不要說希望透過法律或政策來鼓勵民間配合了,這也使何以台灣許多公私建築都不能符合節能減碳的目標。這是典型法律與政策無法配合的情形。我們如果去德國,會發現有些教堂已經使用太陽光電板(VIPV)作為建築物的外牆,這些措施都有賴政策及法律的基礎,但台灣的法律環境始終不利於這樣的發展。
其次是能源政策相關的財稅工具選擇的問題。管制污染氣體排放的政策工具一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以課稅減低排放量,另一種則是管制總排放量,但允許廠商自由交易排放權。這兩種政策工具的選擇,在許多管制議題上會有不同的考慮,在能源管制上也常引發各方不同看法、甚至有相當爭議。能源政策及其政策工具的選擇,與運輸、產業、民生等重要議題等息息相關。在全球產業的發展上尤其明顯,每當能源價格上漲,戰爭與國際政治利益的衝突往往一觸即發。能源價格的波動亦同時影響各國經濟發展、產業結構以及內國對原油的補貼。以臺灣漁業為例,考量到漁民生計及漁業發展,政府大量補貼漁船油費,但同時也造成一定程度的能源使用浪費,使台灣在環境議題的國際互動上面對許多困難。許多政策,單純從內國角度出發是一種思考,從氣候變遷與國際規範的角度切入後,又有不同觀點。有時從內國特定需要出發的政策,在氣候變遷的國際管制下卻明顯呈現缺陷。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使用控制各國排放量的方式,試圖要求各國降低汙染,但此一政策工具背後可能隱藏了國際法與內國法的衝突。究竟要以管制總量或內國課稅為控制污染的最佳工具,還有很多討論空間。舉例而言,全球能源市場機制存在已久,但顯然一直不能從價格機能來促成能源使用的效率,反而長期受到國際政治局勢的影響。因此在1990年代開始思考希望透過能源管制以達溫室氣體減量的政策工具時,最後選擇以總量管制的方式。反觀國內,究應選擇總量管制或課徵碳稅等政策工具,最近也引發許多討論。從國際規範上來看,許多能源市場也受區域政治的影響,控制總排放量的管制方式較能給區域中強勢的國家或機制相應的規範力量,歐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臺灣在政策工具選擇的思考上,因為沒有跨國機制的要求,雖然相對比較具有自主性,但將來還是會受到這些跨國機制的影響,也不可能完全自外於這些跨國機制,應該盡快思考出對應於國際法及內國需求的最適政策工具。
肆、國際規範下的全球能源管制
各國能源政策都必須考慮能源效率與能源安全,但氣候變遷對於領土及生命產生極大的威脅和影響,並有全球連帶的效果。這也使得氣候變遷的全球規範因應,逐漸從單純的政策協調,轉變為具有強制力的法律規範;而因為氣候變遷所生巨災對人類生命安全的嚴重威脅,要求各國減緩、甚或防免氣候變遷甚至可認為是各國在國際法上的義務。循此觀點出發,即使臺灣並非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締約國,仍有遵循此一規範的必要。以UNFCCC為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規範要求,已經從期待一個好的政策制定,或是僅為配合國際合作,轉變為國家必須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及安全等習慣國際法上的義務。這樣一個從政策到法律、甚至進一步到國際法義務的規範變遷,不但實際上已經對國際環境法的發展有所影響,更應該逐步反映在台灣的政策與規範制定之上。
能源管制及能源安全的問題也是如此。能源使用與溫室氣體排放及氣候變遷的議題息息相關。要求各國制定能有效減緩、甚或防免氣候變遷的政策及規範,已經成為各國在國際法上不能推卸的義務。當然,隨著國際規範機制的介入,這些國際規範機制背後的權力結構也將深入影響、甚至控管內國政策,歐盟或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對其會員國的經濟或能源政策,均有不容忽視的影響。我國的再生能源條例是否符合WTO規範,也一直是熱烈討論的焦點。國際規範影響面的加大,會強化國際組織的力量,某程度當然也會稀釋內國的決策權力,稀釋內國政策工具的效果。賦予國際組織過多權力將滲透內國主權,內國權力將面臨被削弱的危險,在目前國際規範機制仍無足夠的透明程序與參與機制的情況下,國際規範的合理性及正當性等問題也會受到質疑。
伍、能源政策的公開透明及其國際面向
臺灣的能源政策經歷了幾次重要的轉變。以往能源局在進行能源決策時會預估能源於未來十五年的走向,並將之公佈於網頁上,但整體而言,我們能源政策的透明化仍然相當不足。我們對於政府採買原油的來源以及相關程序,嚴重缺乏相關資訊。臺灣與印尼及澳洲都有採買原油,但這些原油採買是否有注意到相關內國或國際法上的問題?事實上,能源問題早就存在於國際法面向,也有相對應的法律機制,開採能源所生的國際人權議題亦已層出不窮,例如上述提及之澳洲與印尼,皆曾發生因能源開採所致人權侵害的訴訟。關於人權以外的環境侵害,目前也有許多相關訴訟正在進行。這些議題都將影響國家能源政策,但臺灣尚未將相關議題納入考量。臺灣與印尼也曾就一筆高額煤炭交易發生糾紛,雙方對煤的純度有所爭執,最後以國際仲裁方式尋求解決。類似的問題未來將與日遽增,且非以國內法即能單純處理。在能源政策與法律的思考上,國際規範將愈來愈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臺灣不能再予以輕忽。
發佈於
環境政策法律相關課程
來源
第 4 頁,共 5 頁